李想的6.39億年薪,憑什麼?
作者 | 貝塔商業 阿康
李想拿了6.39億年薪,上熱搜了。然而相比起之前雷軍“疑似”成爲首富時的讚賞,網友更多的是吐槽甚至嘲諷:
“天天虧錢的車企,高管卻年年高薪”
“銷售提成才1200”
“我的理想年薪和李想年薪差不多”。
一時間,喫瓜羣衆將李想連同整個電動車新勢力行業,一起拷打。
這事兒,不只是錢的數字刺激人,更像是大衆情緒的錯位釋放——爲什麼李想掙錢,有人會覺得不舒服?
我認真扒完財報、翻了新勢力們的近況,答案或許在這些真實的對比裏。

李想的6.39億,並不是白拿。這6.39億並不是直接從公司賬戶上打走6.39億現金。這筆錢裏,99.6%是股權激勵,不是現金工資。具體拆開是:
基本年薪:266.5萬元;
期權激勵:6.36億元,源於公司達成2024年交付50萬輛目標;
行權價格:14.63美元/股,而理想當下股價約26美元/股;
實現方式:李想需掏出約19億元現金才能行權。
換句話說,這不是公司送錢給他,而是他自己必須出錢買股票,然後承擔波動,未來可能賺、也可能賠。而這套期權,是2021年就設定的,屬於“達標才解鎖”的里程碑機制。
2024年,理想完成了50萬輛交付,目標達成。那問題來了,原定目標不是80萬輛嗎?確實,公司年中將目標下調到了50萬。很多人就卡在這兒,質疑激勵“自導自演”,對自己下KPI、再自己獎勵自己,程序正義顯得有點弱。
但我們稍後再談程序感受,先看現實的冰與火。
“別人家都在爆雷”理想卻賺錢了

要知道,李想拿這筆錢的時間點,幾乎是整個新勢力行業最難熬的階段之一。
2023年10月,威馬汽車申請破產重整,創始人沈暉被曝出國;
2024年初,高合汽車宣佈停產,創始人丁磊“失聯”;
2024年底,哪吒汽車被曝資金鍊斷裂,裁員風波不斷;
2024年蔚來繼續鉅虧,全年淨虧損約200億元(據財報);
極越汽車崩潰後等待重整,前景堪憂……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這屆新勢力,退潮得尤其快。
但理想卻成了少數“掙錢的車企”之一。2024年財報顯示:
交付量:50.05萬輛(新勢力第一);
營收:1445億元;
淨利潤:80億元。
你可以不喜歡李想,但你不能否認:在一堆企業爆雷,創始人跑路中,他硬是把理想拉成了盈利的新勢力銷冠。
對比一下:
小鵬董事長何小鵬:2024年年薪167.6萬元;
蔚來董事長李斌:2024年仍虧,個人薪資未公佈,但公司虧損擴大;
比亞迪王傳福:年薪765萬元;
吉利李書福:年薪僅37.6萬元(但是真·控股巨頭,早已不靠工資);
是的,李想確實在數字上“鶴立雞羣”,但在兌現方式和風險承擔上,他也的確是“別具一格”。
如果你是李想這6.39億你敢拿嗎?

我們算一下,李想如果真想兌現這6.39億,他得:
1、掏出真金白銀19億美元,行權買入期權股份;
2、拿住這1800萬股,短期不能套現,長期得賭公司持續上漲;
3、假如理想股價掉回行權價之下,他可能血本無歸。
這和“落袋爲安”是兩碼事,甚至更像是一場超級豪賭——用創始人自己的錢,繼續押注自己打造的公司。
這套模式,其實源自馬斯克。特斯拉2021年就給了馬斯克類似的“零年薪+超高股權激勵”模式。中國的新勢力學得很快,但多數車企沒到那一步就死了,李想成了唯一活下來兌現這套玩法的人。
這個6.39億的核心爭議,其實就在這兒。
2021年,理想汽車設定了“里程碑式”股權激勵條款,分階段觸發。其中第一階段條件是:2024年交付50萬輛以上。但問題是,理想原本在2023年底喊出的目標是——80萬輛。
到了年中,公司發佈財報時,目標變成了50萬輛。於是質疑聲來了:“KPI自己設,自己改,再自己領獎,太巧了吧?”、“有沒有程序正義?”、“普通員工拼死拼活25萬,李想一句話就能領6個多億?”

(24年底,李想購買親自在車管所上牌,回應網友質疑:
500萬以內的車,最好的就是理想汽車。 然後他回頭就買了輛298萬的法拉利)
從感受上講,這些質疑並不難理解。但也必須講清楚幾個現實:
第一,理想是上市公司,不是李想一個人的理想。激勵方案不是臨時起意,而是2021年就已披露給投資人的公司治理安排,寫進年報、過了董事會,也通過了股東。不是李想說給就給、說改就改。
第二,目標調整背後有充分理由:2024年初,MEGA車型失利,銷量低於預期,加上新能源市場集體遇冷,理想的策略轉向了“止損與穩增長”。換句話說,不是爲了李想那點股權調目標,而是市場不給力,理想不得不修正航線。
這並不罕見。現實裏,幾乎所有新勢力都“向現實低頭”過——
蔚來2025年一季度淨虧損34億元,全年預計還要燒掉百億;
哪吒、極越、高合接連暴雷,威馬創始人跑路海外,微博淪陷;
即便是小米汽車這類後來者,也在產能爬坡期不敢定太高目標。

(24年3月21日,面對李想maga遇冷的問題,李想發佈員工信)
在這樣的冰面上滑行,還能完成50萬輛交付,逆勢交出淨利潤,成爲新勢力裏唯一盈利的一家。李想這一年,從產品策略到成本控制,確實是一場場硬仗打下來的。
比起那些還在虧損、卻依然高薪的車企高管,這筆錢至少站得住業績邏輯。
爲什麼李想掙錢
大家總覺得“不舒服”?

這可能纔是這場爭議的核心。
同樣是掙錢,雷軍也掙錢,甚至之前網傳差一點登頂中國新首富,但大衆對他的感受,幾乎是“集體祝福”級別的。
小米SU7賣爆了,雷軍的那句“賭上所有榮譽”“人生最後一次創業”,依然能刷屏熱搜,打動人心。
爲什麼?
因爲他太“對味”了——穩重、謙遜,說話總帶點苦口婆心;十年如一日地用“雷布斯”的姿態勤勤懇懇做產品;微博一發就是“加班”、“感謝米粉”、“虧錢也要做好產品”。
這不只是會做產品,更是會做人設。
反觀李想,他從不掩飾自己的“暴脾氣”,面對輿論,有任何不爽,直接對線。說話直接,態度強硬。
那句當年在節目上拍桌子怒喊“聽我講完!”的畫面,至今仍在不少人心中打下了“傲慢”、“跋扈”的烙印。哪怕過去了十幾年,他的樣子依舊——情緒外露、不太迎合、保持自信,但也增長了謙遜。
所以,他很能幹,但不夠“討喜”。
這不是他的錯,只是我們的審美習慣:
我們更偏愛“於東來”式的企業家:低調、溫和、有情懷、有公益心,最好再自帶“奉獻型人格”。
企業家要掙錢可以,但你得“感恩社會”;你可以發光,但不能太鋒芒畢露;你可以有錢,但最好“看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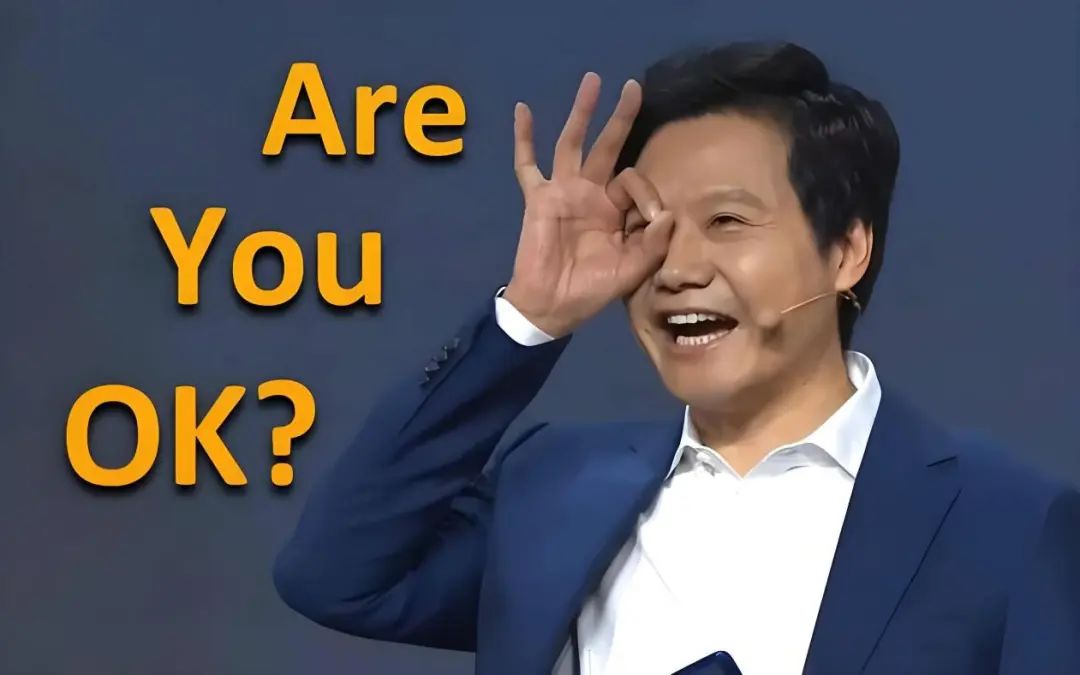
最後講個更大的問題:
爲什麼我們會對別人掙錢如此敏感?
不僅僅是對現實的焦慮。
也許,還有“批判資本”的烙印,“無私奉獻”的集體潛意識,以及鄙視鏈的思維慣性。
但你得承認,掙錢不是原罪,靠本事掙錢更不是。
問題不在李想拿了多少錢,而是我們習慣用“是不是像個好人”的道德尺子,去衡量一個企業家的價值。
而現實是,這個行業活下來的不多,盈利的更少,李想拿錢,是對結果的獎勵,而不是性格的投票。
說到底,我們希望企業家掙錢的方式要“他值得”,而不是“他厲害”。
這其實挺矛盾的——我們一邊喊着尊重市場、尊重創業者;一邊又希望他們像老好人一樣低眉順眼,別讓人有“情緒落差”。
如果今天是個“情商高、話少、衣着樸素”的創業者拿了6.39億,大家或許就笑一笑,“大佬牛逼”,然後就過去了。
這並不完全公平,但確實真實。
是的,我也覺得李想有時候嘴欠,有點粗魯莽撞。但你不能否認,他能在一個高風險、高死亡率的行業站住腳,靠的是戰略、執行力和極致的產品定位的硬實力。
這不是在爲任何人的富人洗地,而是想提醒大家:在評價財富之前,或許我們也該試着理解隨之而來的風險、責任和代價。
質疑是正常的,但理解也很重要。
對創造價值的尊重,是一個社會走向成熟的標誌。
免責聲明:投資有風險,本文並非投資建議,以上內容不應被視為任何金融產品的購買或出售要約、建議或邀請,作者或其他用戶的任何相關討論、評論或帖子也不應被視為此類內容。本文僅供一般參考,不考慮您的個人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需求。TTM對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或保證,投資者應自行研究並在投資前尋求專業建議。
熱議股票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