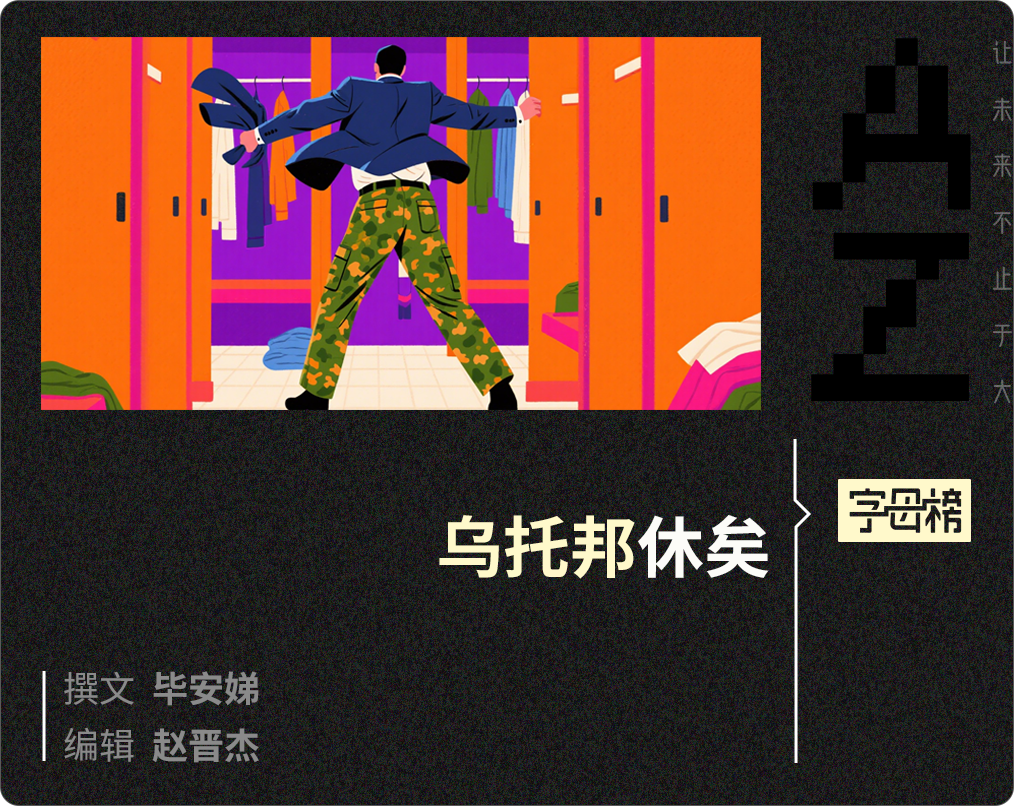
硅谷到底還是大變了。
近期,包括Meta首席技術官、OpenAI首席產品官在內的多名硅谷高管,集體加入美國陸軍。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國防部宣佈,OpenAI拿下了1.2億美元的合約,將爲軍方提供AI。
遙想7年前,谷歌因爲員工抗議,直接取消了和五角大樓合作的Maven項目。去年,當員工再次抗議公司和以色列合作的Nimbus項目時,谷歌解僱了幾十個人。
遙想2年前,研發高超音速導彈的Castelion公司在硅谷開不了銀行賬戶,如今也已經暢通無阻。
放棄抵抗,擁抱政府合約,高呼“維護美國在AI領域領先地位”的硅谷,大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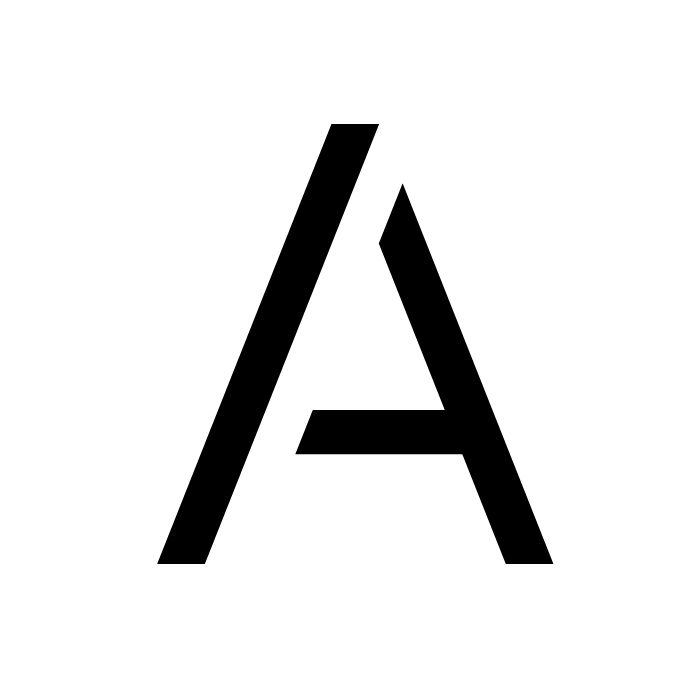
硅谷高管加入美國陸軍,並不是走走形式,也不是裝裝樣子。
美國陸軍預備役專門成立了一個新的創新團隊,代號“201分隊”,其目的很直接:爲軍隊帶來技術升級。
第一批招募的硅谷高管個個是重量級:Meta 的首席技術官 Andrew Bosworth、OpenAI 的首席產品官 Kevin Weil,以及前 OpenAI首席營收官兼現 Thinking Machines Lab 顧問 Bob McGrew,Palantir 的首席技術官 Shyam Sankar。
注意,他們是真的“參軍”了,都被授予了中校軍銜,每年將服役約120小時,參與的項目涵蓋人工智能軍事系統、利用健康數據優化士兵體能等。
與傳統預備役軍人不同,他們可以靈活地進行遠程工作,無需接受基礎訓練,但必須完成體能測試和射擊訓練。
這個消息看起來有些超現實,《華爾街日報》直呼:書呆子大隊來報到啦!

圖源:AI製作
至於目的,當然是美國軍方希望可以藉助科技人才加強其軍事技術。
“我們需要加快步伐,這正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陸軍參謀長蘭迪·喬治將軍說道。該項目旨在彌合“商業與軍事技術差距”,同時幫助陸軍爲未來涉及地面機器人、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協調傳感器網絡的戰爭做好準備。
這還只是開胃菜,未來這個計劃會擴展到所有軍種,覆蓋數千名參與者。這些科技預備役人員將爲商業技術採購提供建議,並協助招募更多高科技人才。
被招募的第一批高管個個都顯得非常興奮和期待。
“可能是我看了太多《壯志凌雲》吧。”Meta的首席技術官Bosworth說道。他身高超過一米九三,被告知身高太高,無法實現年輕時駕駛F-16戰鬥機的夢想。
他還表示,Meta的創始人兼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支持他加入201分隊:“我認爲,硅谷隱藏着許多愛國主義精神,而這些精神正在逐漸顯露出來。”
這句話頗值得玩味,也道出了201分隊所釋放的一個關鍵信號——硅谷文化已經悄然發生巨大的變化。
不到十年前,在硅谷,就連研究可能用於軍事的技術——更不用說服役了——都被視爲異端邪說。
而如今,五角大樓與硅谷之間關係已經大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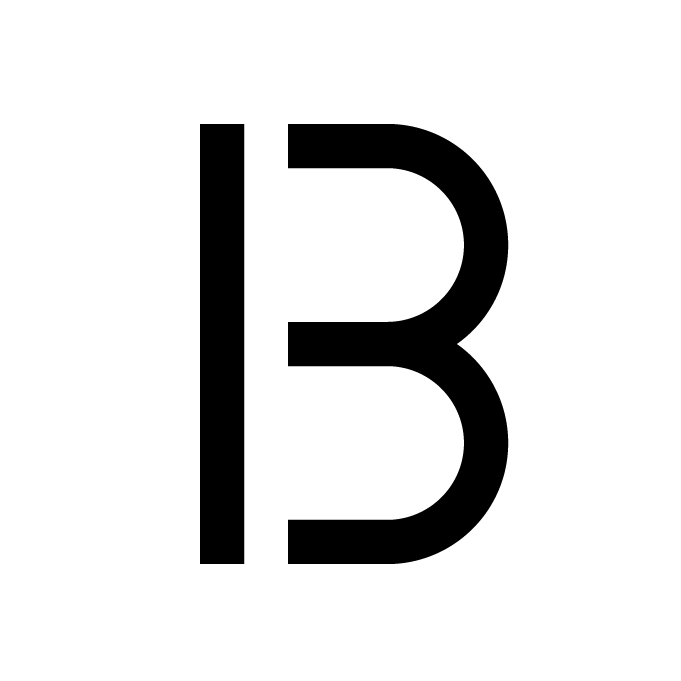
硅谷曾經究竟有多“排斥”和軍事掛鉤呢?
就在兩年前,研發高超音速導彈的Castelion公司仍因製造武器的“污名”,在硅谷連個銀行賬戶都開不了。
硅谷的居民、高校研究者和風險投資人士普遍帶有反戰情緒和烏托邦技術主義傾向,對於“武器研發”的警惕高於全國其他地區。硅谷地區的本地和區域性銀行(包括一些加州銀行及舊金山灣區參與度高的銀行分支)通常對客戶業務性質非常謹慎。
這種文化打從硅谷崛起就定了調。
斯坦福學者萊斯利·博霖(Leslie Berlin)曾在她的著作《麻煩製造者:硅谷的崛起》(Troublemakers: Silicon Valley's Coming of Age)中指出,硅谷崛起的關鍵幾年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而在1969年,美國民衆反越戰情緒高漲,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爆發了大量抗議活動。硅谷的年輕人和權威人士之間有明顯的敵意。
正是這份敵意,促進了硅谷的發展——那些原本打算在國防部或大學實驗室工作的年輕技術專家們決心“走自己的路”,轉而爲獨立的高科技公司工作。
此後數年,硅谷對政治軍事的合作都保持着疏離狀態。
硅谷的文化是明快的、創新的、多元的,公司管理是扁平的、開放的,這似乎與美國政府和軍方天然形成着強烈對比。
2013年美國“棱鏡計劃”曝光,硅谷的科技企業紛紛提高加密能力,公開與美國政府的情報監控保持距離。
和軍方的合作要麼就不會發生,要麼就是公司即便有了這個心思,也會遭遇來自員工和社會輿論的強大阻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谷歌2018年的Maven項目風波。
Project Maven是美國五角大樓的一個人工智能項目,旨在利用機器學習分析無人機拍攝的視頻圖像,用於提高軍事打擊的準確性。
谷歌最初同意參與該項目,但消息傳出後在公司內部引發強烈爭議和道德擔憂。近5000名谷歌員工在內部聯名請願要求公司退出Maven項目,十幾位員工因此憤而辭職。他們還將谷歌的信條翻出來:不要作惡!
儘管谷歌管理層起初辯稱該AI只用於“非進攻性”用途,但未能平息質疑聲浪。
最終在巨大壓力下,谷歌於2018年6月宣佈當前合同到期後不再續約,並立即制定發佈了AI應用的道德指南,明確承諾不將AI用於武器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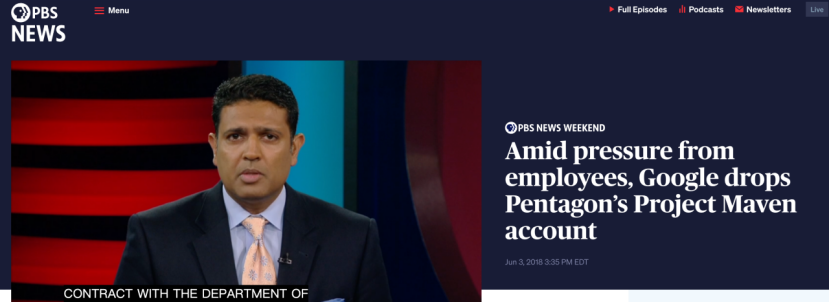
員工大勝利。在當時的硅谷,公司內部的價值觀訴求能夠顯著影響戰略決策。此事件也使硅谷其他企業警醒,軍方合作在輿論和員工層面可能引發的反彈不可小覷。
幾乎在同一時期,微軟子公司GitHub與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有約20萬美元合同,引發 150 名員工公開請願,部分人辭職或參與公開抗議。GitHub雖然沒有因此終止合約,但爲了安撫員工情緒,捐贈了50萬美元給移民權益組織。
在2019年,微軟獲得了價值約 4.8 億美元的美軍增強現實(AR)頭顯合同,也引發了超過 200 名員工聯署請願,稱“我們不是爲了助長戰爭牟利”,要求取消合同。逼得微軟CEO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親自下場表示堅持立場,不會取消合約。
與此同時,也有巨頭在當“異類”,亞馬遜的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就曾明確表示:“如果大型科技公司背棄美國國防部,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困境。”
總而言之,在過去的十年,儘管有不同的聲音,但硅谷文化整體排斥與美國政府和軍方合作。若想那樣做,是會被戳脊梁骨的。
但近兩年,在AI浪潮之外,這套敘事發生了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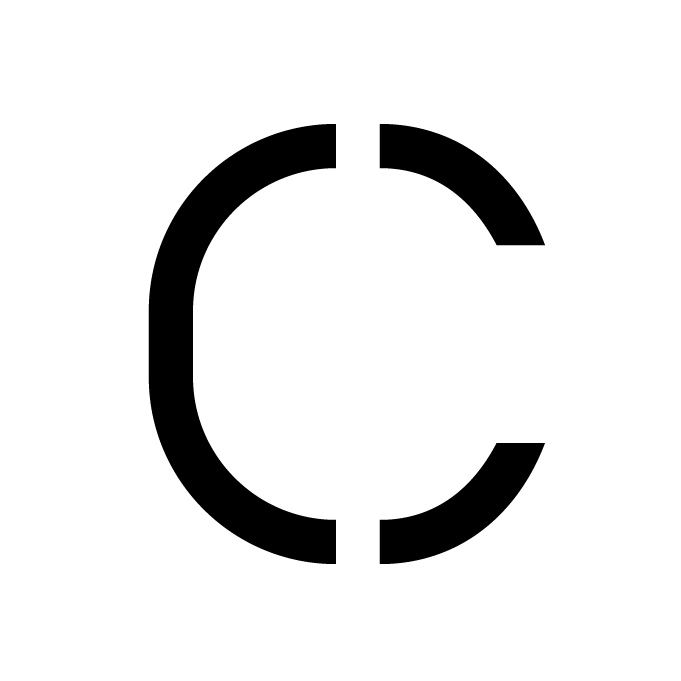
如今包括Castelion公司在內的國防初創公司,在硅谷開賬戶、尋求貸款已經沒什麼難度。這只是硅谷文化變化的一個切片。
以這次有高管加入美國陸軍201分隊的幾家公司來說。
Meta和OpenAI 去年調整了政策,加強與軍方的合作。最近,它們分別與武器製造商 Anduril Industries 合作,爲五角大樓開發產品。Palantir更是已參與國家安全工作二十年。它與美國陸軍合作的人工智能和數據項目價值可能超過 10 億美元。
就在當地時間6月16日,美國國防部宣佈,OpenAI獲得一筆2億美元的合約,將爲軍方供應AI工具。
要討論硅谷文化的轉變,就不得不提到谷歌。
2021年,以色列政府宣佈將價值約12億美元的全國雲計算合同授予亞馬遜和谷歌,爲包括以色列軍方在內的政府部門提供雲基礎設施。這個項目名爲Project Nimbus。
Nimbus項目被披露涵蓋人臉識別等功能,可能用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地區的監控,引發兩家公司內部一些員工的道德抗議。甚至好幾次,有員工在重要的活動場合直接打斷演講,高聲斥責公司的決定。
超過數百名谷歌和亞馬遜員工匿名聯署公開信,呼籲公司放棄該合同。
是的,又是熟悉的配方。這樣的走向,已經在硅谷上演多次。
但與2018年穀歌在員工抗議下放棄Maven項目不同,儘管抗議聲浪引發輿論關注,亞馬遜和谷歌並未退出Nimbus項目。
圍繞Nimbus的抗議一直未停,而巨頭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2024年,在一次百人規模的抗議活動之後,谷歌火速解僱了27名員工。
隨着地緣政治與技術格局鉅變,硅谷科技企業的立場逐漸鬆動。

在互聯網騰飛的時代,硅谷文化迫不及待地和政府及軍方劃清界限——技術是世界的技術。在ChatGPT誕生之後,AI浪潮來襲,硅谷之“我們必須爲美國在AI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而努力”的聲音成爲主流。
這一點,從DeepSeek年初引發震盪也能看出一二。彼時多名硅谷科技領袖呼籲加強美國的芯片出口管制,限制中國在AI領域的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硅谷科技企業在與軍方合作上的態度轉變,是其從刻意遠離政治到投入其中的一部分。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今年開啓第二任期,僅僅是就職典禮,就有多名硅谷領袖捐款。貝佐斯、納德拉、扎克伯格、庫克等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更不必說“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幾乎成爲特朗普的左膀右臂,直接爲白宮效力了一段時間。
大家似乎都在努力忘記,幾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硅谷還在積極抵抗。
從商業的角度來講,硅谷巨頭也有難處。近幾年各國監管機構對科技巨頭頻頻出手,包括谷歌、蘋果在內的巨頭深陷反壟斷泥沼之中。科技巨頭的政府遊說投入在上升,高管與政府也越來越靠近。
與此同時,相比普通消費者市場,政府和國防合同爲科技企業提供了穩定而雄厚的資金支持。美國政府近年來投入巨資支持本土高科技產業(如芯片法案、AI研發資金等),軍方項目更成爲新的“金礦”。
動輒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合約,有什麼不香的?
但即便是局外人遠遠看着,也不免感到唏噓和惆悵。
硅谷終究是變了。
當我們懷念過去的硅谷時,到底在懷念什麼呢?也許是全球曾經近似烏托邦般的科技理想主義吧。
夢醒了,該籤合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