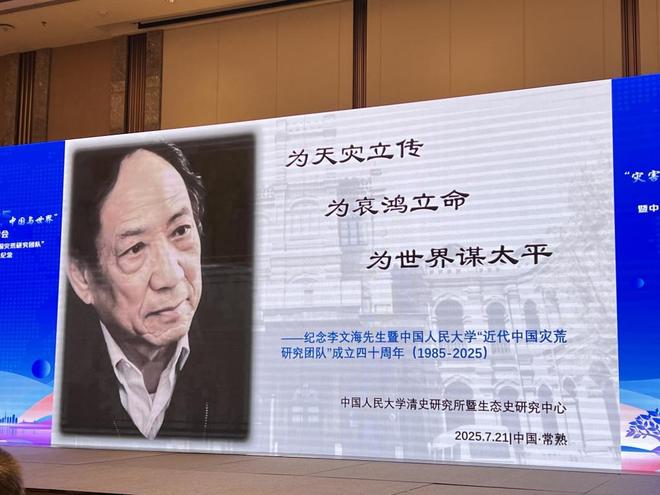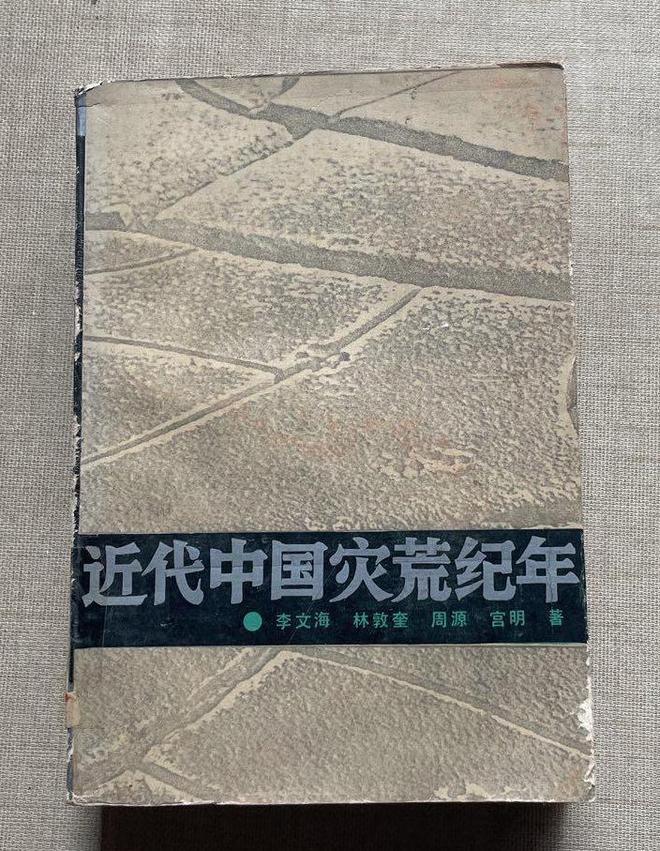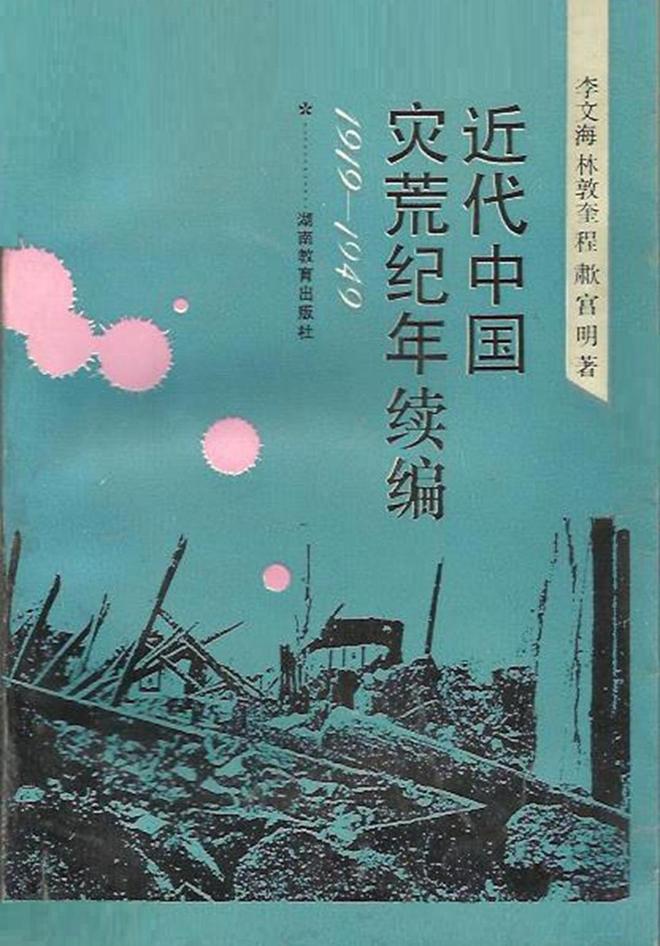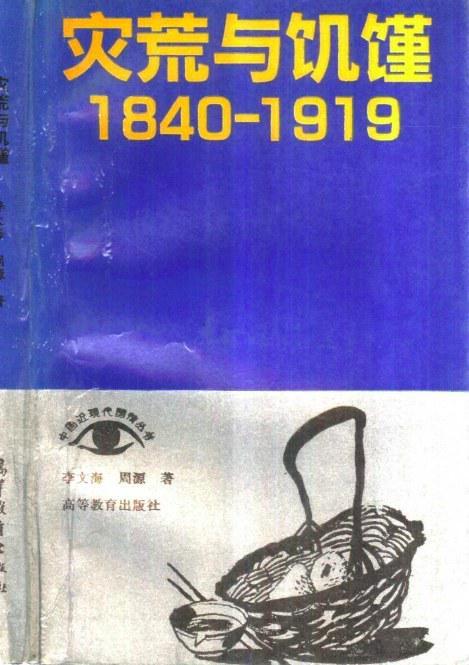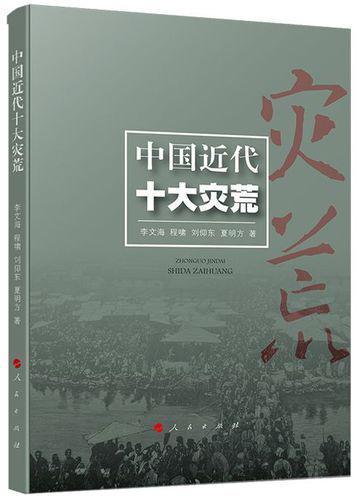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師研報,權威,專業,及時,全面,助您挖掘潛力主題機會!
(來源:澎湃新聞)
近日由蘇州工學院中國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暨生態史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山西大學環境人文與災害治理研究院、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災害史研究新時代: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暨中國人民大學「近代災荒研究團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會在常熟召開。本文系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行龍於7月22日在大會上所做的主旨報告。經授權,澎湃新聞首發。
行龍教授
適應新時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趨勢,「有組織科研」已自上而下地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普遍展開,可謂方興未艾。面對這股新的學術潮流,揣摩「有組織科研」的內涵,我卻自然而然地想起李文海老師。
早在40年前,李文海先生就率先在中國人民大學組成「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着手對近代中國的災荒問題進行研究。40年過去了,由災荒史一路走來的災害史、荒政史、災害社會史,甚至與之緊密聯繫的環境史、生態史已成蓬勃之勢,相關成果蔚為大觀。撫今追昔,此刻我的心緒恰如辛棄疾的名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李文海先生
一
「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是在反思之前史學研究弊端的基礎上成立的。早在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的前言中,李文海先生講到,時下史學研究「存在的幾個主要弊端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簡單化;研究題材的單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他以「題材問題」說開去,認為:
社會歷史本來是五彩繽紛、豐富複雜的,只有從各個不同角度去觀察、研究、分析,才能描繪出真實的、豐滿的、有血有肉的歷史本體來。但我們卻常常只是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歷史的政治方面,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往往只侷限於政治鬥爭的歷史,而且通常被狹隘地理解為就是指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歷史。研究階級鬥爭史,又只注意被壓迫階級這一方。結果,勢必把許多重要的題材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而被忽視的,則要算是社會生活這個領域。實際上,不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做全方位的綜合考察,要深入了解特定時期的社會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
災荒問題,是研究社會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災害不僅對千百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帶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而且從災荒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互相聯繫中,可以揭示出有關社會歷史發展的許多本質內容來。
1980年代,既是一個反思以往撥亂反正的時代,又是一個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的時代。「近代中國災荒史」課題組的成立,給沉悶的中國歷史研究帶來一股新風。回憶往事,我是在1985年研究生畢業前夕,老師帶着我們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訪學,讀到李文海的大作《太平天國統治區社會風習素描》(收入《太平天國學刊》中華書局,1987年版)時,首次看到前引馬克思那句名言的。隨後,我又重讀馬克思的《馬志尼和拿破崙》一文,並在提交給1986年南開大學召開的首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上的那篇論文中,同樣引用了馬克思這句話。再後來,1987年《歷史研究》第1期發表《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編者的話」,也同樣引用了這句話。從此,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成為學者頻繁引用的歷史論斷。
我們知道,中國的史書歷來不乏對各種自然災害的記述,但長期以來卻缺乏對災荒史的系統研究,「災荒史的研究似乎一直是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1938年出版的鄧雲特(即鄧拓)《中國救荒史》,是第一部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觀分析研究自然災害以及人們與之作鬥爭的歷史研究之力作。可惜的是,這部開創性的著作之後,半個世紀多的歲月中,專門的研究幾乎成為絕響。在此期間,雖然也有一些有關自然災害的年表、圖表一類資料書的問世,但或失之於過分簡略,或反映局部地區的情形。總體來看,災荒史研究在那個時期,仍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一個「薄弱環節」(李文海《災荒與饑饉:1840——1919》前言)。「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的成立,無疑是一個「有組織科研」,李文海先生正是組織者和帶頭人。
「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的成立,也是李文海先生對社會現實關懷的產物。中國史學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即史學要有意識地去關注與現實生活密切關聯的問題,讓史學給現實以啓迪。李文海先生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史學家。他並不認為「史學文章只有離現愈遠,它的學術性和科學性才愈高,才能傳之久遠」的說法。他讚成並引用梁啓超在《歷史研究法》講演中的說法:「現代人很喜歡唱‘為學問而學問’的高調。其實‘學以致用’四個字,也不能看輕。為什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什麼做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已」[1]。在他看來,「一般說來,任何一門學問,哪怕是最深奧的學問,如果不同豐富鮮活的社會生活發生緊密的聯繫,不同廣大羣衆發生密切的關聯,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講到「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的成立,他在一次訪談錄中說道:
說起我當初選擇災荒史作為研究方向,不能不聯繫當時的生活環境。1985年,我國改革開放起步不久,人們對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鉅變還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還需要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科學研究特別是人文科學的研究一時變得十分困難,甚至出現了「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教授賣油餅」的現象。「歷史無用論」更是到處氾濫,許多人覺得歷史是老古董,同熱火朝天的現實沒有多大關係,更不能帶來實際的物質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必須要選擇同現實關係密切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課題,用學術實踐證明史學不是「無用」的,不是遊離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外的東西,它可以對社會生活發揮重大的積極作用。我們的課題組就是在這樣的思想下成立起來的。
學術發展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學術,任何一個學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會需求,並且這種需求越來越深刻地為社會所認識和了解時,纔可能得到迅猛的發展和進步。社會需求是推動學術發展和繁榮的最有力的槓桿。[2]
「讓歷史更緊密地擁抱現實」,「社會需求是災荒史學科發展的動力」,「當一個入世的歷史學者」,這就是對社會具有強烈關懷的李文海先生髮出的呼聲,他也以此立題闡述自己的觀點,「強調史學工作要更緊密地結合現實,滿足社會和生活提出的要求」:
我們強調史學工作要更緊密地結合現實,滿足社會和生活提出的要求,決不是要急功近利,重複已往曾經發生過的要求史學研究簡單地為某個具體政治運動或政治口號服務的錯誤。只有在尊重歷史本身的科學性的條件下,歷史研究才能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同時,還應看到,歷史科學對於社會所起的作用,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有些是近期見效的,有些則只在起着「潛移默化」的功效。歷史科學同自然科學不一樣,不能要求一篇論文、一部著作、一個歷史問題的解決,立竿見影地對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生產發生直接的作用。歷史科學研究一不能出糧食,二不能出鋼鐵,但它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誰都一定會承認,沒有全民族文化素質的大幅度提高,「四個現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所以,從總體上來說,一個缺乏歷史感的民族必定是個愚蠢的民族,一個不重視歷史的國家必定是沒有前途的國家。[3]
以強烈的現實關懷從事歷史學研究,是李文海先生治史的特點。早年「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員之一的程歗教授寫道:
文海在課題組建立後就多次強調,要讓史學走出史學家對話的範圍,更有效地為社會現實服務。他認為,繼承古人的有益經驗來豐富當代人的抗災和減災智慧,讓社會上抗災減災、農林水利、土地治理、環境保護等部門的實際工作者獲得災荒史研究的信息,同時又把他們的認識和經驗作為災荒史研究者的豐富源泉,是史學工作者的責任。[4]
二
1985年,「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立後,在李文海先生主持下,並以他為主撰寫了四部有關中國近代災荒史的著作,為災荒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中國災荒紀年》
《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是災荒史研究的第一部奠基之作。李文海先生在該書前言中首先談到課題研究的意義,接着一句「一旦接觸到那麼多大量有關災荒的歷史資料後,我們就不能不為近代中國災荒的頻繁、災區之廣大的嚴重所震驚」,將讀者帶入近代災荒的歷史情景。
他認為,「天災造成了人禍。反過來說,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人禍加深了天災」。政治的腐敗是導致災荒和災荒擴大的不可忽略的原因。從統治者對待自然災害的「措施和辦法」,如報荒、勘災、減徵、緩徵、免徵錢糧;到放賑過程中的「種種弊竇和黑幕」,如賣荒、買災、送災、喫災、急公、勒折、積壓謄黃等,均以舉例來說明。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全面研究和分析有關災荒問題的各個方面,不是靠一本著作所能完成的」:
這本《近代中國災荒紀年》,主要任務只是對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80年時間的自然災害狀況,選擇一些典型的、可靠的歷史資料,加以綜合地、系統地敘述。我們認為,這是一件基礎性的工作,因為不弄清楚自然災害的基本情況,對災害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也就無從談起。我們不知道這部書是否能對社會提供多少有益的幫助,但至少有兩點卻是問心無愧的:一是我們確實還沒有看到哪一本書曾經對這一問題提供如此詳細而具體的歷史情況;二是由於本書使用了大量歷史檔案及官方文書,輔之以時人的筆記信札、當時的報章雜誌,以及各地的地方史志,我們認為對這一歷史時期災荒面貌的反映,從總體來說是基本準確的。就是說,就其基本輪廓來說,是可信的。但是,至多也只能說是總體的「基本準確」和「基本輪廓」的可信,卻無論無何不能說完全的準確和完全的符合歷史實際,因為有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5]
《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
繼《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後,《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1993年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後兩部貫通了自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0年的災荒史。李文海教授在本書前言中,從三個方面概括了後一個時期災荒的特點。這就是,此期政治上的動盪更加嚴重,統治更加脆弱,社會經濟更加凋敝。直接的後果便是大大削弱了社會的防災抗災能力;二是此期兵禍連年,戰亂不已。天災和戰禍往往交相疊見,使廣大民衆雪上加霜,遭受着雙重打擊;三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機構的救荒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失靈,甚至連封建王朝時期有關荒政的一些表面文章也常常顧不上去做。作者清楚地意識到:「災荒史不同於政治史,用政治事件來作為劃分階段的依據,更顯得不合情理」。正是鑑於《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只反映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災荒狀況這一「缺陷」,《續編》與之前後貫通,而且「直接與新中國的歷史連接,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6]
如果說《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及《續編》是資料性的基礎性工作,當然是災荒史研究的開山之作。那麼,《災荒與饑饉:1840——1919》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兩書,則是對中國近代災荒史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之作。
《災荒與饑饉:1840——1919》
《災荒與饑饉:1840——1919》為「中國近現代國情叢書」之一種,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本書簡短的前言部分,李文海教授特別引用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有關災荒的論述:「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衆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佔比較多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在他看來,災荒問題是了解國情、研究國情的一個重要方面。
該書共八章一個結束語。第一章「中國近代災荒與社會生活」,概括性地敘述近代災荒的頻繁與嚴重的災情,加之「人禍加深了天災」,展示了災荒對社會經濟和民衆生活的嚴重影響。中間第二到第六章,將1840年到1919年分為5個時期,分別探討其間的重大災荒。第七、第八兩章,論述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政政策和救荒弊端。以「噩夢醒來是清晨」作為結束語,揭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嚴重災荒帶來的人間悲劇,再也不會重演了。最後的提醒是:「同自然災害作鬥爭,仍然是一個艱鉅而長遠的任務」。全書以災荒為線索,並沒有拘泥於傳統政治史的分期。首尾貫通,敘議相合,是一本「綱要式的近代災荒簡史」。
《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中國近代災荒研究」課題組完成的第四本著作是《中國近代十大災荒》。李文海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講到,前三書,由於體例的限制,沒有對重大災荒展開詳細的描述;又由於題材的原因,讀者對象大抵限於專業研究者。「在廣泛蒐集資料並掌握了基本歷史線索的基礎上,研究就應該向解剖典型、分析個案方面去深入。而如果能夠選擇一個恰當的主題,寫出一部既對專業研究工作者有用,又足以引起專業範圍以外的廣大讀者興趣的書來,那對於我們來說,就不但是更好地盡到了歷史工作者的學術責任,也可以從史學研究和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中得到深切的慰藉」。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本書選擇「鴉片戰爭爆發後連續三年的黃河大決口」「1855年黃河銅瓦廂決口前後」「咸豐七年的嚴重蝗災」「光緒初元的華北大旱災」「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災和甘肅大地震」「1928年至1930年西北、華北大饑荒」「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災」「1938年的花園口決口事件」「1942年至1943年的中原大旱荒」等「十大災荒」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書後附錄「中國近代災荒年表」,更便於讀者從中了解中國近代的災荒全貌。
黃興濤評論上述兩部研究性的著作認為:「通過這兩部專著,人們可以對近代中國的災荒史得到有點有面、全面深入的了解」。他同意學界的看法,認為課題組完成的四部著作,「可以說對中國近代的災荒歷史勾畫了一個完整的輪廓」[7]。
在李文海先生的主持和帶領下,「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不僅完成了四部奠基性的災荒史著作,而且在研究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了一批學術新人,在災荒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相關的研究領域。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李文海、夏明方、黃興濤主編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續編》,全書煌煌十卷。「這套書的出版,以及已列入計劃的後續系列的出版,給近代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基礎性資料,在近代社會史資料的整理出版上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意義。此套書甫一出版,在學術界就產生了較大影響。」[8]
李文海先生對《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鑑價值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該書的前言中指出,《叢編》收錄的調查資料:
不僅僅是因為調查的涉及面極其廣泛,覆蓋着全國絕大部分省區的包括城鎮鄉村在內的自然環境及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更主要的原因還是這些調查大多數都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如現代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法和手段調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調查報告甚至學術論文作為最終的成果形式,這樣既保存了大量的調查數據和原始資料,又凝聚了代表當時比較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各種自然、社會及政治、經濟等問題的分析、透視以及為解決這些問題所提出的對策和建議,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借鑑價值。[9]
對我而言,《叢編》一個值得關注的興趣點,在於從災荒史進而社會史一路演進的學術脈絡。李文海教授評論《叢編》時講到,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作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從學術角度而言,經過已往的研究,一些基本問題已經釐清,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認識,因而需要進一步向社會史這一更廣闊、更深入的領域拓展」。他敏銳地認識到,此前的社會史研究表現出兩種傾向,「一個是無限擴大,一個是無限縮小」:「社會史也面臨着無限擴大的問題。所有的歷史都是社會史,這好像提高了社會史的地位,但實際是取消了社會史的特性,反而不好。這是一個傾向。另外一個傾向,就是將社會史研究零碎化,認為不要去研究宏觀問題,只具體研究問題就可以了,研究社會史就是研究具體問題史。這是一個方面的問題」。他特別強調尊重中國歷史學重視史料的傳統,尊重前人的成果和科學勞動。「社會史離開田野調查、社會調查就很空洞。現在很多人忙於建立自己的體系、自己的框架。實際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師們沒有跳出田野調查的範圍,而且這個調查不像今天的調查,學術大師們田野調查的方法應給我們以啓示。」[10]
在我的認知中,災荒史與社會史緊密相連,李文海先生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大約在20年前,我曾就李文海教授的《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寫過一篇讀後感,在此不以累贅,摘抄一段:
李文海先生治中國近代史和社會史累年,但他並沒有提出過對中國近代社會的驚人理論觀點,也幾乎未曾參加近年來中國近代史領域一些熱門話題的討論,在我看來,大概也算不上那種「著作等身的大師」,但他那種開拓創新又不張聲勢,既不囿故更不媚時的治學精神卻使我感觸良深。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史研究已成為中國史學園林中的奇葩,短短十餘年間,中國社會史由恢復到發展,由稚嫩到健長已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新課題的開拓,新成果的問世也足以使人目不暇接。文海先生雖不聲言社會史,但視野所及、論域所涉卻多為社會史、尤其是中國近代社會史長期被忽略卻又非常重要的課題。以愚陋知,收入本書的《太平天國統治地區社會風習素描》、《戊戌維新時期的學會組織》、《義和團運動時期社會心理分析》等均成文或發表於80年代。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太平天國、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都是學界用力頗多、成果豐碩的領域,以此作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範疇已屬慣見,幾為定框。李文海先生卻能獨闢蹊徑,開拓創新,從社會史的角度開掘了研究領域的諸多空白。以開篇《太平天國統治區社會風習素描》為例,該文「從社會政治生活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深入剖析了太平天國統治區的宗教活動、服飾裝束、婚喪禮儀、過節度歲、天國諸禁等五個方面的歷史,由此折射的正是倡導「自下往上看」的社會史的豐富內涵,由此反映的正是太平天國統治區人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習俗和生活方式的真實面貌。題目不妄稱研究而名曰「素描」,足見其嚴謹的治學之風。文海老師是恢復發展中國社會史研究最早的、身體力行的開拓者之一。[11]
三
1985年,由李文海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迄今已成立整整40年。當今社會,雖然人類對付各種自然災害的政策措施及技術手段在不斷進步,但自然災害仍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嚴重問題,也許是一個要長期面臨的問題。追憶往事,面對未來,重新閱讀課題組成立以來的諸多成果,我們不僅深切緬懷李文海先生的開拓之功,而且為中國近代災荒史的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感到欣慰。這個「進一步的發展」當然與當年的篳路藍縷前後相續,密切相連,也給當下「有組織科研」以很多有益的啓迪。
「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立後,非常注重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以說,課題組成立伊始,即是從有關資料的整理做起的。在李文海看來:「這個工作做不好,不在這方面花力氣,研究也好,著書立說也好,都是沙上建塔,沒有根基,即使勉強寫作,也是空中樓閣、水上浮萍,很不牢靠的。」[12]前述《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及其《續編》,嚴格說來,是中國近代災荒史的資料長編,也是一個奠基性工作,至今仍是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之後,經過前後十年的努力,課題組又完成了1300餘萬字的《中國荒政書集成》,全書共分12冊,收錄宋至清末民初歷代荒政文獻187種,基本囊括了目前所知海內外較為重要的、珍稀的荒政專書。書後附錄《清末民初以前中國荒政書目》收錄492種書名和版本,為研究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國荒政書整體狀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定程度上也成為這個領域「字典式」的工具書。
李文海先生在談到《中國荒政書集成》這部大部頭的書時,曾很有感慨地說道:
歷史學同其他所有學科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其他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一般來說,其研究對象都是現實存在的東西,即使比較抽象的哲學、宗教學等也是如此。唯獨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已經逝去了的東西,是不可再現的往事,所以,史學工作者只有通過歷史資料才能接觸到自己的研究對象。這就決定了歷史資料的整理對學科建設的特殊重要性。目前,就災荒史來說,資料整理工作大大滯後於學術研究工作,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學科發展的一個瓶頸。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事,投入的精力和財力多,遇到的困難和麻煩大,許多人不願意或不屑於做這種事情。我們在編這部書的10年間,就有過很深切的體會,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確實經過了很多曲折,當然也得到了許多朋友的熱情幫助。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我想,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個意思是,學術不是學者個人自娛自樂的東西,它必須要有益於社會,服務於社會,學術成果要能為社會所共享。現在,壟斷資料、封鎖資料的現象十分嚴重,這對學術的發展極為不利。我們想為改變這種風氣做一點努力。另一層意思是說,學術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努力就可以做好的,必須要得到各個方面的支持和幫助。這一點,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在過去,也許靠某個人,十年寒窗,畢生心血,青燈黃卷,皓首窮經,可以產生出了不起的學術成果。今天則完全不同了,如果沒有學術界同行以及社會各個方面的關心和支持,要做出一點學術成績是難乎其難的。我們在編這部書時,就有很深的感受。[13]
從系統整理災荒史和荒政史的資料出發,進而進行科學、深入的研究,是「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一個基礎。
「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立後,並沒有囿於就災荒而災荒,而是隨着研究工作的逐漸推進,步步深入。值得注意的是,李文海先生特別強調災荒史研究的「五個結合」:社會科學工作者同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結合;學術研究的開拓創新同歷史資料的發掘整理的結合;基礎研究同應用研究的結合;中外學者的結合;學術工作者同實際工作者的結合。[14]它曾很有信心地說到,「依靠學者們潛心鑽研、深入探索、勇敢創新,努力做到這五個‘結合’[15],我們完全有理由信心十足地判斷,在新的世紀,災荒史的研究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成績,開創新的局面」!
我們高興地看到,2012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生態史研究中心。李文海先生的高足夏明方教授任主任,李文海先生、美國環境史學會前主席唐納德·沃斯特任名譽主任,災荒史的研究由災荒史、災害社會史、生態環境史一路走來,顯示出更為廣闊的學術前景。
「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立以來,李文海先生就十分重視學科建設中人才的培養。學科發展的基礎在人才,人才培養恰是李文海教授非常重視的工作。他對學生的培養又是十分開放和包容的。他曾經對學生講到:學術的發展需要正常的學術批評,而不是一味地承襲和讚譽;學生可以不讚同老師的觀點,更可以對老師的觀點見解提出批評,乃至於爭鳴。夏明方在紀念文章中曾以「學術內訌」為小題,談到李老師和他及朱滸師生三人就「義賑」問題「有過多次討論和交鋒」,感佩「對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先生同樣抱持海一樣的胸襟。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始終堅持唯物史觀,但他從不會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16]
程歗教授在紀念李文海先生的文章中講到:
「文海帶出了一支思想活躍、人員精幹的研究隊伍。按他的設想,課題組由災荒史為研究方向的專業人員組成,他們不在人數多而在精,成果不在量而在質。再由他們聯合對災荒史有興趣的其他研究者,在各自的專業方向上找到可以和災荒史結合的切入點,共同推動這項研究走向繁榮。現在清史研究所該課題組的學術骨幹是文海的學生夏明方和朱滸。夏明方的碩士論文研究光緒初元的丁戊奇荒,還參與撰寫過《續編》和《十大災荒:;他的《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入選1999年全國首屆一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該文原題為《災害、環境與民國鄉村社會》,「環境」這個醒目的關鍵詞,反映了課題組認識的推進。當年課題組創建時,朱滸還是「紅領巾」,他在2006年出版的《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一書。綜合了博士論文和博士後研究報告成果,以晚清新式義賑為個案,對諸國國家和社會、傳統和現代、「衝擊-回應」和「中國中心觀」、地方性和普遍性等在史學界流行的理論與方法展開了頗有新意的辨析。劉仰東多次和其師合作撰寫過社會史的論文和專著,也是《十大災荒》的著者之一。[17]
程歗先生的文章中還提到,「文海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從事過災荒史研究」。陋見所知,李文海先生指導的博士生和夏明方教授指導的博士生中,仍有許多從事災荒史及其與之緊密聯繫的相關學科的研究。
一個學術單位,僅靠一兩個人的孤軍奮鬥是難以持續發展的,必須有一個有生氣、有活力、有凝聚力、有戰鬥力的學術團隊。這個團隊的人際關係是民主的、生動活潑的、團結和諧的。在學術問題上,在工作問題上,大傢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不同意見都可以心平氣和、暢所欲言地討論,成員之間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大家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小事不計較,淡然處之。我很慶幸我們課題組成員都能向這個目標努力,這是我們這些年能夠做出一些成績的重要保證。[18]
這是李文海先生組織「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並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經驗之談,也是今天「有組織科研」應當汲取的寶貴財富。
斯人已逝,薪火相繼。李文海先生是中國災荒史研究的拓荒者,也是40年前「有組織科研」的組織者和身體力行者。災荒史研究從一枝獨秀到如今的萬紫千紅,李文海老師可以含笑九泉了。
紀念「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成立40年,我猛然想起組織者李文海先生。以上僅為重讀先生著述時寫下的一點讀後感,忐忑不安有之,懷念之情更深。
註釋:
[1]李文海:《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二)》,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官網,2013年6月30日。
[2]李文海:《史學要關注現實,尊重歷史——李文海教授訪談錄》,見《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3]李文海文集編委會編《李文海文集》卷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版,第60頁。
[4]程歗:《史界領袖,治學報國》,見李文海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李文海紀念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05頁。
[5]李文海:《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
[6]李文海:《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
[7]黃興濤:《歷史並不遙遠——李文海教授的學術追求與歷史研究》,見李文海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李文海紀念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72——173頁。
[8]李文海:《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一項奠基性工程——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見《光明日報》,2005年11月24日。
[9]李文海、夏明方、黃興濤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前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李文海前揭文,見《光明日報》2005年11月24日。
[11]行龍:《深入剖析上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李文海先生《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讀後》,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2]李文海:《史學要關注現實,尊重歷史——李文海教授訪談錄》,見《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13]李文海前揭文,見《史學月刊》3013年第7期。
[14]李文海主編《天有凶年》前言。三聯書店2007年版。
[15]李文海前揭文,見《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16]夏明方:《為哀鴻立命——著名災荒史專家李文海先生瑣憶》,見《李文海先生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李文海紀念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55——156頁。
[17]程歗前揭文,見李文海紀念文集編委會編:《李文海紀念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05頁。
[18]李文海《史學要關注現實,尊重歷史——李文海教授訪談錄》,見《史學月刊》3013年第7期。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