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t New Hit Song on Spotify? It Was Made by A.I.
懷揣夢想的音樂人正藉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創作歌曲,部分作品還登上了排行榜榜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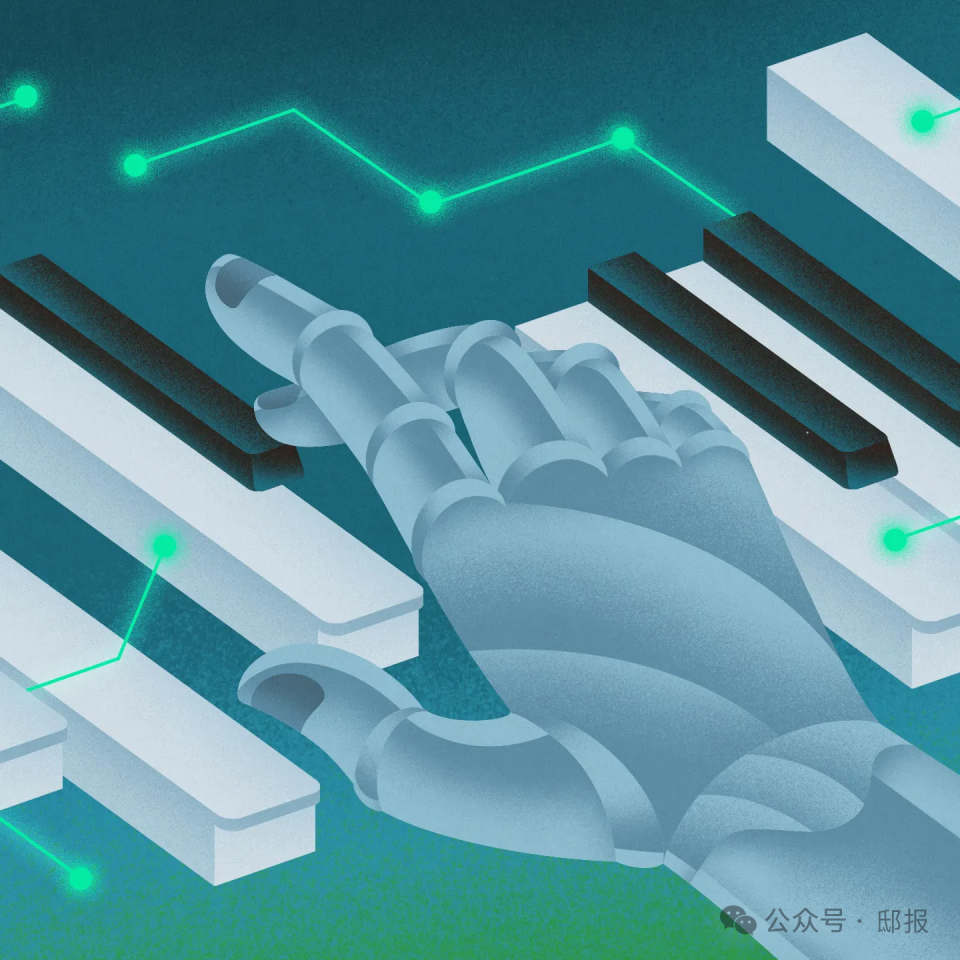
作者:凱爾·查伊卡
2025年11月12日
尼克·阿特(Nick Arter)現年35歲,居住在華盛頓特區,他從未通過傳統方式真正成為一名職業音樂人。他在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長大,家中充滿音樂氛圍。父親和繼父癡迷於90年代的嘻哈音樂——比如Jay-Z、Biggie、Nas,幾位叔叔則是職業唱片騎師,專門播放70年代的節奏藍調。青春期時,他和表兄弟們開始錄製自己的嘻哈曲目,起初用卡帶錄音機,後來換成台式電腦,模仿當時走紅的少年說唱歌手Lil Romeo和Lil Bow Wow。大學期間(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音樂始終是他的愛好。畢業後,他曾短暫嘗試職業化,在當地演出中售賣混音帶,之後在哈里斯堡的一家政府呼叫中心任職。這份工作最終讓他獲得了華盛頓特區德勤公司的職位,而阿特仍會在夜晚和周末繼續說唱創作,卻從未發行過任何作品。「作為說唱歌手,我年紀已經有點大了,」他最近回憶道。直到去年年底,他開始使用人工智能創作歌曲,短短幾個月內,他的作品就在流媒體平台上成為熱門,播放量達數十萬次。或許他的音樂生涯終究還是到來了。
阿特的成功象徵着人工智能正加速進軍音樂行業。如今,沒有任何文化或娛樂領域能免受人工智能影響:可口可樂剛推出了一部採用人工智能視覺效果的聖誕廣告;好萊塢也在大肆宣傳人工智能演員。但這項技術對歌曲創作的影響尤為迅速。幾年前,少數人工智能歌曲因模仿Jay-Z和Drake等流行歌手的嗓音等技巧而走紅。如今,我們正處於人工智能音樂的全面爆發期。本月,一首名為《Walk My Walk》的人工智能鄉村歌曲(帶有打擊樂般的拍手聲和「不喜歡我的說話方式就滾開」這類平淡無奇的歌詞)登上了公告牌鄉村數字歌曲銷量榜榜首,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突破300萬次;這首歌的表演者是一個名叫「佈雷金·拉斯特」的方下巴數字虛擬形象。9月,密西西比州一位年輕詩人創造的人工智能節奏藍調歌手克桑妮婭·莫內,在多首歌曲登上公告牌排行榜後,簽下了一份數百萬美元的唱片合約。今年早些時候,一支名為「絲絨黃昏」的神祕迷幻樂隊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突破100萬次後,創作者才承認這支樂隊是「合成的」。Spotify並未對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進行標註,該公司表示正在改進人工智能過濾系統,但並未明確界定何為人工智能歌曲。過去一年,該平台已從其服務中移除了超過7500萬首「垃圾曲目」,但仍有無數未標註的人工智能歌曲存在,而且許多聽衆無法分辨其中差異。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者成功區分人工智能生成音樂與人類創作音樂的概率僅為53%。
如果你在網上聽到一首人工智能生成的歌曲,它很可能是用兩款熱門音樂創作應用中的一款製作的——Suno或Udio。阿特的創作過程會同時用到這兩款應用。他通常在手機上寫下自己的歌詞,然後結合歌詞和對設想中歌曲的備註擬定文本提示詞,將提示詞輸入兩款應用,對比哪款能產生更好的效果。(阿特告訴我,「一個好的提示詞應包含(年份)、(音樂類型)、(樂器配置)、(曲風)和(情感)。」)他會通過這種方式為每首歌生成幾十個版本,反覆調整旋律和樂器配置,直到滿意為止。最後,他使用Midjourney為每首新單曲創作專輯封面——通常是普通靈魂樂歌手的特寫肖像,再將歌曲上傳到YouTube和Spotify等流媒體平台。他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掙脫那些破事》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接近90萬次,這首歌融合了70年代末節奏藍調抒情曲的風格與嘻哈式的抒情勵志元素:「今年我狀態正佳/那些阻礙我成長的破事都見鬼去吧。」這些應用允許阿特保存風格快捷操作面板,方便他日後快速創作類似風格的曲目。「算法會 kind of 摸清你的喜好,」他解釋道。阿特以「Nick Hustles」為藝名發行的音樂絕非含蓄之作(另一首歌名為《Stop Bitching》:「沒人能靠/像個小屁孩一樣抱怨變富」),其樂器伴奏和人聲中都帶有人工智能音效特有的空洞單薄感。但旋律——以及某些抒情亮點,比如《Dopest MotherFucker Alive》中醒目的髒話——足夠抓耳,讓人過目不忘。
這項技術「開闢了新的創作可能性領域,」阿特說。他從未是一名技藝嫺熟的歌手,如今卻能涉足自己從小聽到大的老式節奏藍調。突然之間,他可以塑造永恒的虛擬形象來代表自己的音樂,配上虛構的背景故事,而非展現自己日漸老去的千禧一代形象。僅在過去一年裏,阿特就創作了約140首歌曲,他並不隱瞞自己的音樂是由人工智能製作的,不過不知情的聽衆可能不會注意到他的YouTube賬號名「為文化而生的人工智能」。他的許多歌曲都像是關於日常生活的俏皮吐槽:「唱的都是堵車、奇波雷快餐弄錯訂單這類事,」阿特說。他的作品包括《全食超市裏的健康女孩們》《我要去睡覺了》,以及《我得戒菸了》和《我他媽又把電子煙弄丟了》,這些歌曲迎合了他所在的受衆羣體,涵蓋了成癮的各個階段。他從未為自己的人工智能音樂做過任何營銷或推廣,但口碑傳播和算法推薦(比如Spotify的電台功能)將他的作品推向了他少年時說唱夢想中的流行高度。賈斯汀·比伯曾用阿特的歌曲為Instagram帖子配樂,50美分則發布過一段自己在車裏跟着尼克·哈斯特爾斯的歌曲哼唱的視頻。說唱歌手揚·薩格借鑑了阿特歌曲《我的兄弟們都很頂》中的副歌部分,用於自己的熱門曲目《想念我的兄弟》,並將阿特列為詞作者。阿特得以辭去諮詢行業的工作,開啓了全職「半自動化音樂人」的職業生涯。他現在與音樂發行商UnitedMasters合作,從50多個不同的流媒體平台獲得收入。此外,他還為客戶的生日或婚禮創作定製歌曲,每首收費500美元(若客戶提供歌詞則半價)。阿特堅信自己所做的只是一種新的藝術創作方式:如果你的音樂「能改變某人的生活,」他說,「它是否由人工智能創作真的重要嗎?」
儘管人工智能音樂廣受歡迎,但以大多數標準衡量,人工智能並非優秀的歌曲創作者。正如倫敦音樂人兼製作人艾哈邁德·科爾多法尼(他也使用人工智能創作)所說:「人工智能作品中存在一種刻板感,一種深層次的空洞。」科爾多法尼注意到許多人工智能生成歌曲都有一個奇怪的共性——平淡乏味:它們單調且缺乏結構,沒有清晰的副歌、旋律走向或高潮部分。「有時候人工智能分不清橋段和副歌,」科爾多法尼說。他補充道,作為聽衆,他在人工智能音樂中找不到那種「被觸動」的感覺。正是看到了這項技術的短板中蘊含的機遇,科爾多法尼開拓了一份蓬勃發展的事業:幫助懷揣夢想的音樂人「人性化」他們用Suno、Udio等應用製作的歌曲。雷·薩巴赫是他的客戶之一,這位蒙特利爾攝影師創作拉丁風格的說唱和舞曲。薩巴赫先生成歌曲(有時會使用人工智能創作的歌詞),然後使用科爾多法尼根據他本人真實錄音訓練出的人工智能聲線模型進行演唱。(薩巴赫說,朋友們聽到這個「虛擬的他」時,根本分辨不出差別,還補充道:「有時候這真的很嚇人。」)如果人工智能聲線在某些地方出現瑕疵,科爾多法尼就會插入薩巴赫本人的真實錄音——這個過程雖然繁瑣,但仍比從頭錄製更快。最終的作品悅耳動聽,比阿特或佈雷金·拉斯特的歌曲更具人情味,不過受歡迎程度也低得多。
Spotify的聽衆是否在意他們聽的音樂是否「人性化」?隨着人工智能的主流化,合格質量的歌曲可以被即時、無限地生成;這種無摩擦的大規模生產,再加上通過算法推送進行傳播,意味着人工智能生成的音樂與網上其他類型的社交內容並無太大區別。音樂的質量或持久性次要於其短暫的衝擊力;核心目標是實現「聽覺吸引力」。這些音樂可能過目即忘,但如果聽衆只播放一次——而且他們很可能只會播放一次,因為除了新鮮感之外,這些音樂沒有太多深度——而創作者又能立刻再批量產出十首歌曲,那也就無關緊要了。對於懷揣夢想的音樂人來說,這個新生態系統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民主化機遇。「我認為人工智能確實有機會打破行業壁壘,」阿特說。在他的歌曲成為流媒體熱門之前,唱片公司根本不關注他;如今他表示自己收到了不少合作邀約,但會觀望一段時間,直到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未來更加明朗。他承認,考慮到Spotify上充斥着大量垃圾歌曲,行業准入門檻可能過低——用戶試圖查找某首普通爵士樂背後的音樂人時,往往只會發現一個匿名虛擬形象,名下有數十張同年發行的器樂專輯,這讓用戶感到困惑。阿特說,那些音樂垃圾製造者「不重視創作本身」;他們的作品背後沒有歌詞、沒有人物形象、沒有明確的創作意圖。他認為自己對人工智能的運用遠高於這些行為。「我不會做那種工作,」他補充道,「我太愛音樂了。」♦
本文作者:凱爾·查伊卡是《紐約客》的專欄作家。他的專欄「無限滾動」探討了塑造互聯網的人物和平台。他的著作包括《過濾世界:算法如何扁平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