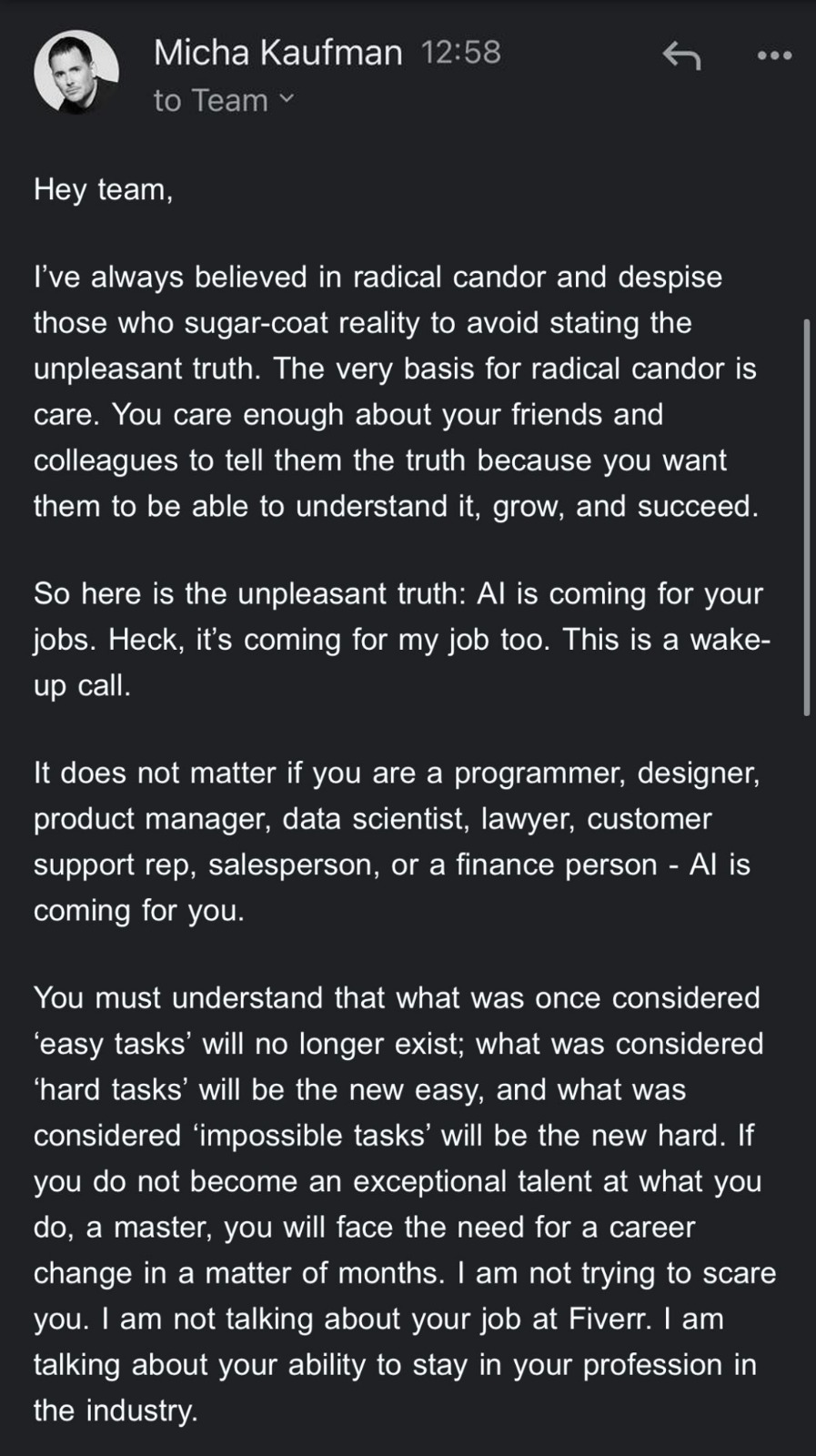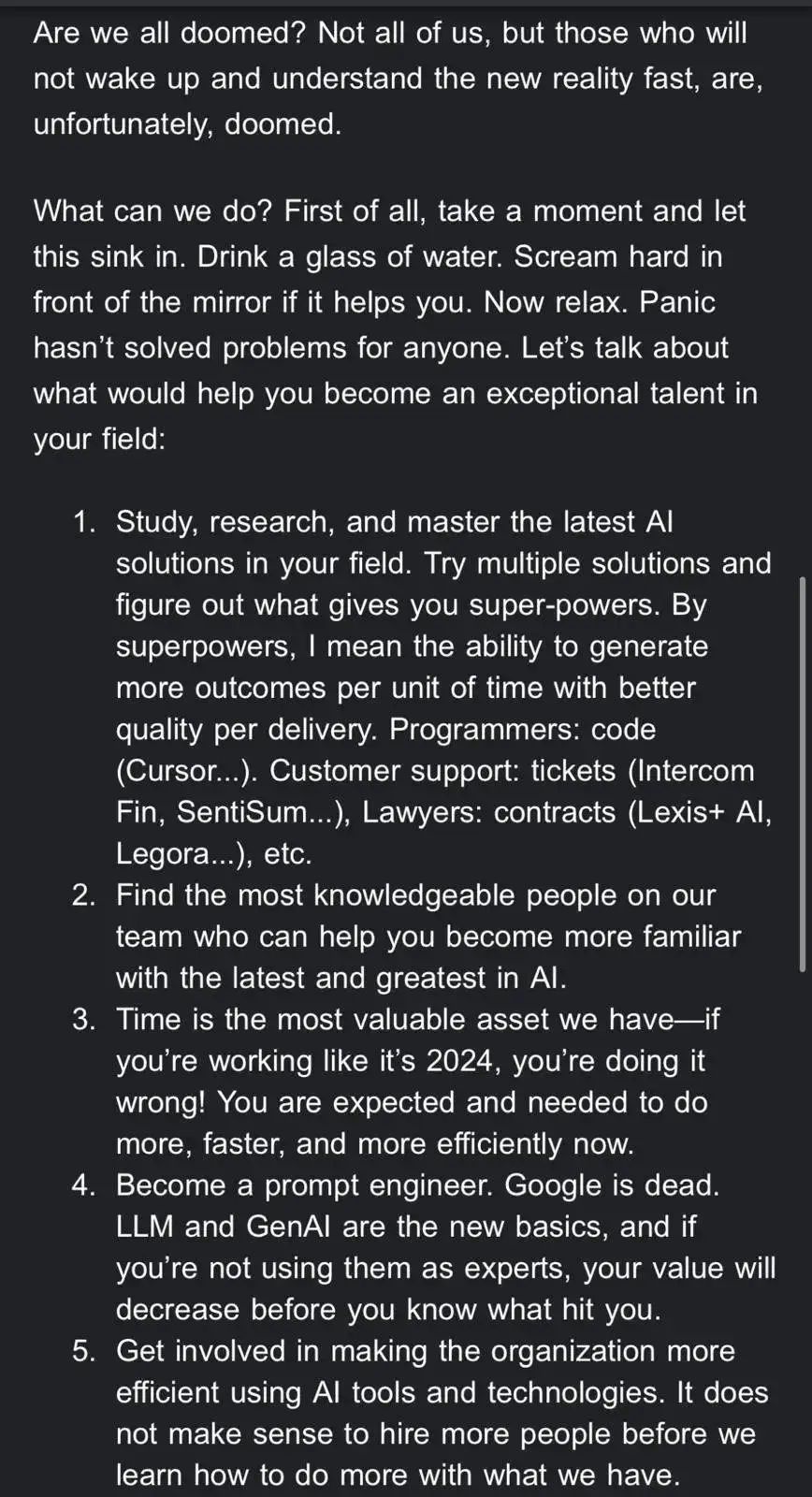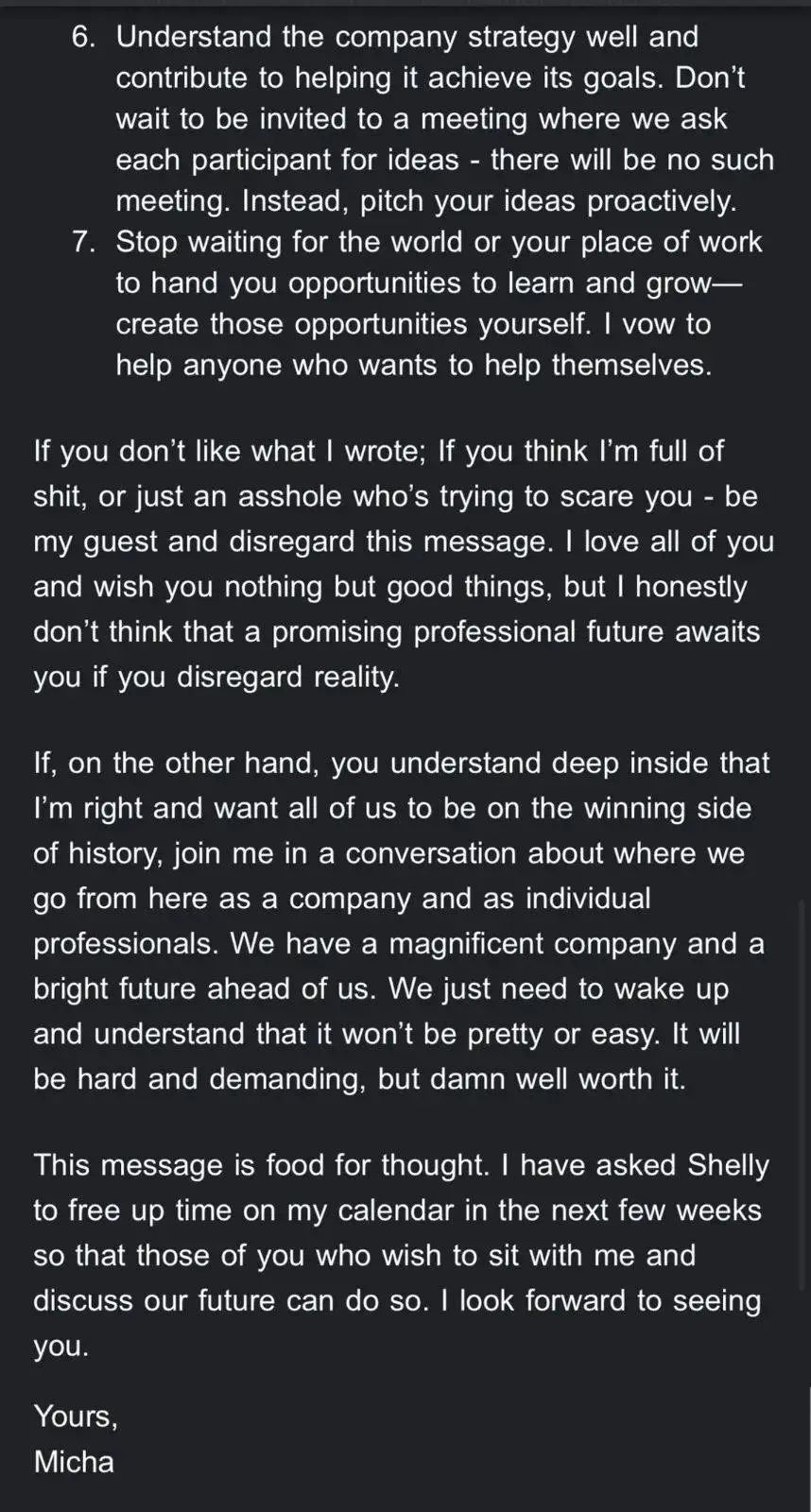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格基金,作者:Neya,编辑:Cindy,原文标题:《Fiverr CEO 内部信曝光后万字回应:99% 的 AI 公司都是泡沫》,题图来自:AI生成
今年 4 月,Fiverr CEO 在 X 上发布的一封公开信迅速刷屏。
他直吐真言:AI 正在抢你的饭碗。不管你是程序员、设计师、产品经理、数据科学家、律师、客服、销售,还是财务,AI 都会找上你。
过去那些“简单任务”会消失,“难题”将变成新常态,“做不到的事”会成为下一轮的挑战。如果你还不是这个领域的高手,很可能几个月内就得考虑转行。
这段话直白、不留情面,却也点中了当下对 AI 与工作的集体焦虑。或许正是这种身处浪潮中的危机意识,让 Micha Kaufman 带领 Fiverr 一路踩中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风口。
2010 年,正值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过渡,O2O 模式和零工经济刚刚兴起。这一年,Micha Kaufman 和 Shai Wininger 联合创立 Fiverr,搭建了一个连接自由职业者与服务需求方的在线“打零工”平台。起 Fiverr 这个名字是因为平台刚成立时,购买任何服务都只需要花 5 美元。
2013 年,Fiverr 推出 iOS 应用,正式接入移动互联网;2017 年起,Fiverr 接连收购视频创作平台 VeedMe、内容营销平台 ClearVoice 和数字营销机构 SLT Consulting,扩张社交媒体营销服务边界。
他收购过 10 家公司,每完成一次收购,Fiverr 都会更新一版内部的“收购手册”。这套流程从来不是从交易谈判开始,而是从第一次对话开始。Kaufman 曾说:“如果你在 Day 1 就没把整合放在脑子里,那基本上就输了。”
2019 年,Fiverr 以 6.5 亿美元市值上市。次年,全球疫情爆发、远程办公兴起,Fiverr 迎来业务暴涨,全年营收达 1.895 亿美元。
但在 AI 时代,人们还需要打零工吗?在新一轮技术更替下,我们该如何保住饭碗,又如何持续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Micha Kaufman,一个信奉技术驱动的创业者、一个帮助无数自由职业者找收入的人、一个天使投资人,将聊聊 AI 时代的新工作、新能力和新价值。
本次内容来自 20VC,以下是真格编译全文。
一、AI 正在抢走你的饭碗
Harry Stebbings:你最近给团队发了一封邮件,说:“AI 正在抢你的饭碗,说实话,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一记警钟。”你为什么想发这封邮件?
Kaufman 发布在 X 上的公开信全文
Micha Kaufman:其实这个念头在我心里酝酿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出于一种挫败感,看到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场“觉醒”正在发生。
我跟团队说得很直接,不加粉饰,只是想把一些想法抛出来,看看能不能引发讨论。于是我让 Chief of Staff 订了一间能坐 50 人的会议室,发了封邮件,说我会在那里带着电脑待 3 个小时,谁想聊就来坐坐。
结果到了那天,我一走进去,至少挤了 250 个人。我压根没准备讲什么,原本只是想随便聊聊,最后变成我一个人在那儿把脑子里的想法一股脑倒出来。
Harry Stebbings:我们能不能聊聊你当时那段讲话?我们都说话挺直接的。我想问的是,当你看到 Chegg 这种在线教育平台几乎被 AI 替代,外界也开始说 Fiverr 会不会是下一个,你在跟那 250 个人讲的时候,讲了什么?
Micha Kaufman:我当时讲得也挺直接的。我告诉大家:理想情况下,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设法把自己 100% 的工作内容自动化掉。你可能做不到,但目标就是 100%。
听到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没用了?如果我能把工作全自动化,公司还需要我吗?
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如果你能自动化掉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意味着你释放出了 100% 的时间,可以去思考那些无法被自动化的事情。
你可以把时间用在非线性的思考上,可以参与公司的战略讨论。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写那封邮件时,才突然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当我们真正理解 AI 是怎么扩展我们的能力、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它其实也在倒逼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人”的价值。
当功能性工作被机器替代,什么还能让你与众不同?是你对美的认知?对是非的辨别?还是你的创造力和跳脱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你?
AI 正在逼我们重新认识人性本身。
Harry Stebbings:你刚才提到要重新理解人性,而人性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脆弱和恐惧。我们会本能地回避那些看起来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东西。我 10 分钟前刚从一个董事会下来,会上有位 CEO 说:“我的团队不愿意拥抱 AI,他们害怕,觉得 AI 迟早会取代他们。”作为 CEO,应该如何推动 AI 的使用,且不让团队陷入恐惧?
Micha Kaufman:那我只能说得更直接一点。你看,在高科技行业,很多人年纪都很轻。我自己做公司快 30 年了。刚开始工作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持续为别人创造价值。
但过去十来年,不知从哪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公司有责任帮你变得更好。我跟团队讲得很清楚,这完全是错的。
你人生中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伴侣、更好的父亲,靠谁?靠你自己。那为什么在职场里,你却觉得我应该为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员工负责?
说实话,如果你不愿意花时间提升自己,不愿面对现实,那你完了。我没有义务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
但我会为什么人负责?我会去帮那些愿意成长、愿意面对这个过程的人。如果你愿意帮自己一把,那我就在你身边。这是我的承诺。但如果你不想,那你可以走了。不是你在 Fiverr 完了,是你这个人完了。
以后不会再有公司愿意雇用一个连自我成长都不愿意的人。时代已经变了,每个人都得想清楚,自己的时间要用在哪里。
Harry Stebbings:你刚刚说的这段话,我一边听一边在想,“不,我完全不同意!”就像在婚姻里,伴侣之间也会互相推动、帮助彼此成长。但你说得也没错,一切的前提还是要从自己开始。
Micha Kaufman:但如果你自己压根不想变得更好,连最基本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愿意投入,那别人帮不了你。我可以为你提供成长的资源,但我不是你爸,我不对你的人生负责。
二、有了 AI,人们还想工作吗?
Harry Stebbings:说到这儿,我想问个可能有点悲观的问题。我和 Jason Lemkin(SaaStr 创始人)是朋友,他最近也在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工作了,热情和投入都不如以前。你怎么看?你觉得,有多少人是真心愿意拥抱 AI 带来的变化?
Micha Kaufman:如果你只从当下的视角来预测未来,那注定是错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景模糊、瞬息万变的时代。现在的局面和当年的互联网泡沫有点像。那时是“.com”,现在是“.ai”。
我每天都会刷到 40 多家初创公司。现在,每个人都在试图应对信息泛滥的局面。
但我不认为这种混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目前的状态太不稳定了,所以以现在的标准来判断未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至于人们还想不想工作,答案很简单:看你是谁。如果你不想工作,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可以离开,我也不会花时间去帮你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只基于一个假设来运营团队:那些愿意工作的人,不管是为了生计、自我表达,还是寻找意义,他们自然会留下来。
我们这一生,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工作。如果工作没意义,生活会非常痛苦。如果你不想工作,那你要么会变穷,要么就成了社会和父母的负担。这也是所谓的觉醒。你得醒一醒,开始长大。
人类的本性就是竞争。我们从生物本能上就需要去争取资源、延续后代。你想开快车、坐商务舱、不想排队。这些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得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我在意的是工作的意义。
三、克隆时间归零,AI 泡沫要破裂了吗?
Harry Stebbings:这也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我可以承认自己在哪些方面经验不足,而你有 30 年的积累。所以我想请教你,你说现在的 AI 创业潮像是当年的互联网泡沫。那你在当下看到的哪些迹象,让你判断这就是个泡沫?
Micha Kaufman:我刚才提到,我每天都能刷到四十多家新创业公司。这个市场根本装不下这么多玩家。事实上,这波泡沫早在 8~10 年前就开始了。
很多公司在抢同一批客户,做的也都是差不多的功能。这其实就是供过于求。一个市场能容纳的公司数量是有限的。
市场出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有时是一批公司直接倒下,有时是几家整合。但在很多垂直领域,比如网络安全,最后能留下来的,通常只有一两家。赢家拿走一切,其他人什么都拿不到。
现在的环境完全变了。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概念,叫“克隆时间”:如果你做出一个不错的产品,别人复制你需要多久?
25 年前,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年,还得看你做的有多复杂。我们 15 年前做 Fiverr 时,有人要抄我们,可能也得花 6~9 个月。但今天,有了 AI,这个时间缩短到了十天,甚至更短。对一些简单项目来说,门槛几乎为零。
每天都有无数新产品被造出来,但它们大多没有差异,也没有真正创造增量价值,基本上都是重复已有的东西。
还有一个现象,不好量化,但挺值得聊的,就是产品的“广度”。以前你要做一个完整的产品,就像在爬珠穆朗玛峰,要花很长时间准备,一步步往上走,好不容易登顶后才发现,还有十座山等着你。
但现在,AI 就像是给你装了电梯,不论你是用 Lovable 还是别的工具,都能一下子把你送到离山顶 300 英尺的地方。你可能轻轻松松就做出了一个还不错的小产品,甚至站上了山顶。但真正的挑战,其实从地面才开始。你要怎么推广?怎么拉用户?怎么形成护城河?
我姐姐也做了个 App,挺好。但这就是 AI 时代的真实写照:人人都能做点什么,但这些东西的价值可能接近于零。
Harry Stebbings:我想追问一下你说的“克隆时间”。像 Fiverr 这种平台,真正的价值不在前端长什么样、支付系统怎么做,而在于品牌、分销渠道、和服务方之间的信任。这些东西才是别人最难复制的部分。那在你看来,复制的速度还重要吗?
Micha Kaufman:你说得没错,但这里面还有个 but。我们在 Fiverr 成立不到九个月的时候,市面上就已经冒出大概 30 家模仿者。几年后,这个数字变成几千家。
当时我们团队内部争论很激烈。一派说要主动出击,搞定所有抄袭者。他们觉得这样不公平,别人怎么能直接拿走我们的创意和努力。
但我更倾向另一种看法:我们其实有两个核心优势。
第一,我们是最早一批做这件事的人,而且跑得够快。我一直觉得,创业就是一场赛跑。你跑步的时候只能盯着一个方向:要么向前冲,要么回头看。但如果你边跑边回头,就会慢下来,甚至摔倒。所以你必须始终盯着终点,不断加速。
第二,我们真正知道自己在解决什么问题。别人可能复制了表面,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有你说的那些“魔法”:产品、渠道、品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九个月的先发时间,而那九个月里,我们在播种。播种品牌,播种影响力,搭社区,这些事情复制不了。
但如果今天你能在十秒钟内复制一个成熟产品,那还有谁愿意花时间自己从零做起?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成功就更依赖运气。运气当然重要,但没有先发优势的创业者,得非常非常幸运才行。
而现在很多创业者,其实只是把已有产品做了一点点边缘上的微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问题意识也不够清晰。那你做的东西小,结果自然也小。
所以我之前说,AI 逼着我们重新认识人性。今天的创业公司应该认真想清楚:我为什么要创业?不是为了做某个产品的“X.1 版本”,也不是为了做出“下一代”而去做,而是去解决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
四、产品复制越快,创始人越重要
Harry Stebbings:我也在做投资,每个赛道可能都投了 20 多家。比如我最近投了一个 LLM 优化引擎的项目。现在每个方向里都有几十家公司,不像十年前可能只有两三家。你作为投资人,会怎么判断、怎么筛选?
Micha Kaufman:说到底,还是要从底层看今天这轮技术变革。
技术如果完全民主化,它就不再构成优势。2022 年 11 月 OpenAI 推出产品的那一刻,它的 GTM 实际上就已经极度民主化了,因为它是免费的。你没法比免费更自由。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变得更聪明了:写得更快、研究得更深。但别人也一样。AI 拉高了大家的能力,也把所有人拉回了同一起跑线。技术越来越强大,但它没有赋予你独特优势。真正的差异,回到了最本质的问题:人是谁。
技术会演化,商业模型会变,方向也会转型,但最后做决定的是人。所以我回看每个项目时都会想,创始人是谁?他们有没有天分?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做的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还是带着信念?能不能面对变化?能不能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想问题?
我投过几十家公司。最成功的几个项目,很多是我一开始并不看好的,因为看起来问题太难,市场太小,团队内部还有各种问题。但他们有非常强的人。
Harry Stebbings:有具体例子吗?哪个你原本并不看好,后来却大成?
Micha Kaufman:有一家已经上市了。当年是种子轮投的,方向特别难,问题也难,创始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没捋顺。说实话有很多理由它该死掉,但它没死。
Etsy 的一个投资人形容他们那家公司时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之所以投这家公司,是因为它至少应该死过七次,但它没死。”这一点最能让我看见团队的力量。
我跟他们有一段时间几乎没联系,结果突然有一天说要上市了。我当时心想:不会吧?这也太神了。最后这个项目给我带来 50 倍以上的回报。所以说到底,还是人最重要。
Harry Stebbings:我常说,看早期项目只看三件事:创始人对不对,方向对不对,交易合不合理。这三个都对,那就该投了。
Micha Kaufman:我同意。这套判断逻辑从来没变过,也不会变。
五、99% 的 AI 公司都是泡沫
Harry Stebbings:你刚刚用 .com 泡沫来类比现在的 AI 热潮。那你觉得,接下来几年我们会经历类似的泡沫破裂吗?还是说,核心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会让这轮热情和融资维持下去?
Micha Kaufman:如果你问我,现在这 1000 家 AI 公司里,999 家活不过一两年。市场是很无情的。
我之前说过,大多数公司并没有提出真正有趣的问题,也没做出足够有价值的创新。他们只是看见风口就扑上去。这本身没错,但最终市场会出清,就像 .com 那一轮一样。
但那些真正解决问题、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会穿越泡沫,比如当年的 Amazon。在这波 .ai 浪潮里,也一定会诞生新的核心玩家。现在可能已经能看出一些影子了,虽然还说不准谁会成为下一个 Google。但路径是类似的,从 CPU 到 GPU,应用会迎来一波发展。只是现在判断还太早。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会先迎来一次出清,先从投资人开始。到某个时间点,他们会说:“我退出,钱不投了,你们自己先搞清楚在做什么吧。”这会让市场枯竭。
今天做一家 AI 公司,会遇到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你怎么获得用户注意力;第二,你如何留住他们。这两点上,绝大多数公司是失败的。
我们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现有的市场容量远远不足以容纳现在这么多玩家,而用户真正愿意掏钱买单的产品,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两件关键东西缺失了:监管和贵的技术。这里的“贵”不是指几十块或几百块能买到的技术,而是那种真正昂贵的、高壁垒的基础能力,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承担得起。这些技术才会真正拉开差距,也是市场完成自我清理的另一条路径。
六、版权已死,我们还为何创作?
Harry Stebbings:你觉得当下最有趣的问题是什么?
Micha Kaufman:很多,比如我们是否已经接受了“真实已死”?我们是否还能分辨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别?但还有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在这个被技术重塑的世界里,人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我的观点是,你、我、包括所有人类,过去一直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如果这是前提,那一切就该围绕我们运转。但我们能接受自己失去这个中心位吗?
AI 正在吞噬整个世界。它会持续进化到一个阶段,不再需要人类监管或干预。尽管它是基于人类创造的内容训练出来的,但它未必在乎我们。它学习我们创造的一切,把它们混合,然后生成新东西,不告诉你是谁的,也不承认是谁的。
比如现在有人用 Harry 的内容做播客,听上去还不错,但说白了,它只是生成了点东西。让我真正担忧的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人类继续创作、继续分享的动力会从哪来?如果一切都被吞掉、混掉、抹去来源,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内容?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反馈。我们希望自己的创作被看见、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开源代码,为什么我们会主动分享。因为别人的进步也建立在我们的努力之上。但如果最终什么都没有留下,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Harry Stebbings:但现在不少 AI 生成的内容,比如短视频,质量也不差。为什么你觉得它们没有价值?
Micha Kaufman: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创作者。当优质内容被 AI 拿去训练,而创作者得不到任何署名、反馈或收益,这场游戏就变味了。版权已经死了,在一夜之间。
Harry Stebbings:怎么理解版权已经死了?毕竟现在音视频内容还是有很多。
Micha Kaufman:从人类历史来看,智人大约 30 万年前出现,进步长期是线性的。直到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它让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人变得有知识、有表达,也因此开始创作。印刷术让作品能被复制、被流通,从而启发更多人。
1710 年,英国颁布《安妮法案》,这是现代版权制度的起点。它的出发点很简单:如果你想鼓励人们创作、分享,就要给他们两种权利:第一,署名权,你的名字该出现在作品上;第二,变现权,你能通过作品赚钱。
这套机制维持了 500 年,支撑了整个现代媒体产业与互联网生态的发展。
但现在,AI 跳过了这一层。它既不引用来源,也不给署名,直接把内容吞掉、揉碎、重组。版权在实质意义上已经死了。
如果原创者得不到承认,也没有激励,他们还会创作吗?还会公开分享吗?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不是以 Fiverr CEO 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父亲。
过去 500 年,我们靠着创作与分享才让生活变得更好。我不希望这条路就此中断。人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像我们现在做播客,把内容交给 AI 用,是你自己决定的,这是选择。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为人类生产内容,而是为机器,那我们就真的失去了中心。
Harry Stebbings:你对 AI 的看法非常坦率、直白,几乎毫无保留。作为 Fiverr 的 CEO,你觉得自己有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发声吗?我知道很多上市公司 CEO 都在 AI 的使用上面临不小的压力。
Micha Kaufman:我不觉得那是压力,更像是一种责任。历史上,曾经的巨头公司如今遍地尸骸,没能活下来,大多是因为扛不过技术浪潮。
过去一轮技术周期可能还能撑个 7~8 年,现在呢?浪和浪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你得看清下一波浪在哪里,才能踩对节奏。
作为 CEO,你的任务就是在每次技术变革里找机会,再谈下一步。但大多数公司做不到,哪怕是已经很成功的公司。很多连第一波浪都还没抓稳,就被卷走了。
Harry Stebbings:那你在准备下一波浪潮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Micha Kaufman:有人问过我,现在做 CEO 是什么感觉?我说,就像你在暴风雨里当船长,然后有人问你:“你当船长感觉怎么样?”
很湿、很黑,一英里之内什么都看不到。
七、摩尔定律已死,AI 时代快是唯一出路
Harry Stebbings:你真是这么想的?回头看你在 Fiverr 的 15 年,现在这个阶段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Micha Kaufman:我父亲在半导体行业做到过很高的职位。那个行业几十年来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它遵循摩尔定律。只要摩尔定律不失效,你就可以推演出未来 10 年的计算能力会达到怎样的程度,芯片能做到多小。这是一种确定性,我们甚至有些怀念那个时代。
我们有一套清晰的推演逻辑。而现在,变得太快了。每次有人问我“你觉得五年后行业会是什么样?”我都会笑。你可以有方向感,但谁要是说他能精准预测五年后的 AI,那他多半是看不清现实。
Harry Stebbings:为什么这个问题让你觉得可笑?我反倒觉得向前看是应该的。就像有人问谷歌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2030 年的搜索引擎长什么样?”他直接说:“我不知道,我们就一年一年往前看。”
Micha Kaufman:我们当然要一直问这些问题,但也要明白,当下这个混沌时刻不适合做线性预测。噪音太多了。
Harry Stebbings:但现在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这样的一大堆开源模型,你不觉得整个 AI 行业已经开始商品化了吗?
Micha Kaufman:我不这么看。我们还没到 AI 真正进入定价阶段,也还没到 AGI,更别说超级智能。我们确实离得不远了,但还没到。所以现在其实是企业下场试水的窗口期。
Harry Stebbings:你怎么看现在价值越发集中这件事?比如 Anthropic、OpenAI、NVIDIA、TSMC、Google、Meta、微软这些万亿市值的 0.0001% 超级玩家好像统治了一切,其他公司几乎都在边缘。你担心这种鸿沟吗?
Micha Kaufman:这和云服务市场没什么本质不同。你看 AWS 和 Azure,其实也早就是寡头格局了。云服务供应商一大堆,但真正占 80% 市场份额的只有两家半。这种势头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Harry Stebbings:你会考虑让公司上市吗?
Micha Kaufman:当然,为什么不呢?
我其实挺支持上市的,有很多理由,只是要选好时机。但如果你还以为上市后能操控市场情绪、左右股价,那我建议你别上。这是个糟糕的想法。
对于那些有长期思维、愿意做长线博弈的人来说,上市是个不错的选择。
Harry Stebbings:但我听说资本市场最看重的是“可预测性”,甚至超过一切。这不就意味着,反而很难支持那些看不到短期回报的长期项目了吗?
Micha Kaufman:如果你资本结构稳,能持续创造自由现金流,那你就能靠自己驱动增长。如果你的执行力强,市场对你有信心,那即便你想做些激进的事,融资也不会太难。
Harry Stebbings:五年后,你们会有更多工程师还是更少?
Micha Kaufman:大概率会更多。
技术把竞争拉回了起跑线。你现在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但你的竞争对手也能。那你要怎么办?你得做得更多,跑得更快。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公司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速度。就是真能推动事情快速落地的能力。
八、速度与方向合一,才是真动能
Harry Stebbings:那有没有一种情况是,越多反而成了负担?比如 HubSpot 最近就说,他们写了太多代码、做了太多功能,根本没法上线,反而拖慢了进度。你怎么看?
Micha Kaufman:能做更多,不代表你就该不停做。这很关键。
所以我在团队里从来不用“speed”这个词,我用的是“velocity”(速度矢量)。速度加方向,才叫真正的动能。
你跑得再快,方向错了,也只是在原地打转。比如你写了一堆代码,结果推不上线,那说明问题根本不在产出,而在于你没有先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
你真正的优先级错了。不是一味往上堆功能,而是该先问一句:我们现在到底被什么卡住了?与其建一大堆东西,不如先把基础设施搭好。
而且说实话,你很可能也在做一些根本没必要的东西。停下来,不要浪费时间。
我之前在一次团队会议上也说过这事。那封邮件发出去之后,250 人全都挤到一个会议室。我当时就在思考“动能”这个词时,想的是怎么能持续降低失败的成本。
说到底,大多数公司所做的事情,最终都会失败,只不过没人会主动讲一个失败的故事。
像 Amazon 这种量级的公司,可能同时在跑 5000 个实验。都失败了,也没关系。但要是你投了 10 个工程师,搞了 3 个月,最后发现方向错了,那就太晚了。如果你只花了 1 个人、3 天,快速验证失败,那其实是件好事。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降低成本,这样我们就能多试错。我经常在想,怎么把单位时间的产出翻倍、甚至翻三倍,同时还能提升交付的质量。但你能这么想,别人也能。大家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那怎么办?你得有额外的差异。
我觉得,开发者这个职业接下来会变得非常不一样。AI 将会让那些已经是 10x 的人成为超级开发者,而不是用来让普通人从 1x 成长为 10x 开发者。
九、市场营销将最早被 AI 颠覆
Harry Stebbings:如果未来工程和技术团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你觉得今天有哪些职业,五年内可能就不存在了?
Micha Kaufman: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客服,但我自己在 Fiverr 看到的最大变化,其实是在市场营销部门。
如果你仔细看那些 copilot 工具在干什么,它们做的,恰恰是工程师最不想做的那部分:到处找开源代码、复制粘贴、查文档、找库、评估能不能用、审安全问题、fork 再自己改。这一整套流程,本质上就是 Google 检索加复制粘贴,机械又重复。你会觉得,这是人该干的吗?这应该是机器做的事。
但营销不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一款 AI 工具,能像对工程师那样,对营销人产生同等级别的赋能。
说到底,我们还是在向人做营销。不管是图文、音视频、脚本、文案,最终都得被人类感知,被人类理解。这就要求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的行为,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
但问题是,很多人被 AI 工具给诱惑了,以为一切都能自动化,结果方向错了。AI 没有你想得那么全能,至少目前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Harry Stebbings:完全同意。我花很多时间研究社交媒体传播。但说实话,如果你是在 Virgin、NatWest、Chase Bank 这些大公司里写“我们很高兴宣布新品上线”这种文案的,那你完了,AI 十秒就能写十条。
但如果你是那种擅长做病毒式传播的高手,对语境很敏锐,知道怎么抓住热点、善用 meme、搞得懂梗图,还能写出有张力的内容,这就是真本事了。现在我愿意花一百万美元请这样的人帮我管社交媒体都找不到。
Micha Kaufman:没错。所以我觉得,在所有岗位里,初级市场职员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比程序员还快。因为程序员哪怕用 AI 写代码,最后也得看懂那段代码,调试它、跑通它,就算是新人程序员通常也能理解逻辑。
但市场营销不一样。AI 介入之后,基本没有门槛了。这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自动化程度最高,变化最剧烈。
Harry Stebbings:你在管理风格上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因为 AI 的兴起,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或沟通方式?
Micha Kaufman:我不用 AI 来写作,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跟其他上市公司 CEO 聊过这事,甚至还开过玩笑,说干脆我们自己做一个 AI 投资者关系助手得了。这样连电话会都不用开了,致股东信也不用写了,AI 自己写自己答。
反正这些材料很大一部分是给机器看的,用来跑交易、做情绪分析。那干脆喂一个标准格式进去,更高效。
Harry Stebbings:在你和其他 CEO 私下交流时,你们是更倾向于认为,AI 的进展其实比大家表面上意识到的更快,失业潮会更早到来?还是觉得还早,没有大众想象得那么强?
Micha Kaufman: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理性预设是:我们距离大规模失业那临门一脚,不远了。
当然,如果 AI 其实没那么快,那太好了,大家还能喘口气。但如果它真的很快,那你最好早点开始准备。这是更安全的做法。
现在还没有公司因为 AI 进行大裁员。但本来就臃肿的组织已经在动了。
我自己在邮件里也提过:在我们说要招更多人之前,先看清楚现有这批人有没有真正把潜力发挥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团队结构要保持轻巧,但不能短板明显。如果有一天真要砍成本,你得非常清楚,哪 50 个人是你第一时间可以放手的。如果你心里已经有名单,那不如早点行动。
我们要先搞清楚如何把现有团队的产出最大化,再决定是否招人。如果真要招人,那这些人必须是 AI native 的。
无论你来的是法务、财务还是客服,你得对这个时代的运作方式了然于心。我不会从头教你。
Harry Stebbings:那有没有一个你最想削减的成本,但现在因为某些原因还不能动的?
Micha Kaufman: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削减市场营销的成本。但前提是,你的业务能在没有营销的情况下自然增长。
如果你的自然增长能力足够强,你就会开始问自己:我现在花这一块钱带来的新增客户,真的值得吗?
我之所以还没砍,不是放不下,是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点。
十、快问快答
Harry Stebbings:你对 AI 的哪一个看法发生过转变?
Micha Kaufman:最初 AI 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 OpenAI 以非营利的方式推动这项技术。当时我以为,这会是一场全球协作的变革,能把技术的权力下放,让更多人掌握,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现实很快让我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当 OpenAI 开始转向付费模式之后,我意识到事情不会是我想的那样。作为一项底层技术,我本希望它能更开放一些。
Harry Stebbings:Elon 明显支持开源,Sam 支持闭源。你更倾向哪一边?
Micha Kaufman:AI 是一项非常基础的技术引擎,从我的角度看,我还是更支持开源。
Harry Stebbings:假设你有个孩子刚大学毕业,正准备进入职场,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Micha Kaufman:我会在他上大学之前就给建议,别上大学。
除非你去大学是为了谈恋爱、社交、喝酒,那就另说。如果你需要有人每天催你起床、逼你上课、用考试吓你才能学东西,那大学可能是你需要的。
但现在 90% 以上的新兴职业都可以靠自学,还省时间。不喜欢看书?可以看视频。不想看视频?可以听音频。再不行,AI 可以按你的需求生成。在我看来,大学只是在浪费时间。
Harry Stebbings:回顾 Fiverr 的历史,有哪个机会你没抓住,现在还后悔吗?
Micha Kaufman:我们曾经有机会做出 OnlyFans,但我们当时选择了不做。
其实在 Fiverr 很早期的版本中,我们就看到一些端倪。当时我们并没有开放那类服务的品类,但后台的搜索里开始频繁出现一些暗语。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去 Fiverr 搜 X,懂的都懂。
我们当时是能做的。但从创始人的角度,那不是我们想走的方向。
Harry Stebbings:Fiverr 会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家公司吗?
Micha Kaufman:我不知道,现在是。但我每年会花一两天给自己做一个“领导力审计”。
我会问自己:我还适合继续领导这家公司吗?我会评估我的能量、投入、好奇心和产出结果。如果对公司已经贡献不了最大价值,那就得面对现实。
我有个规则:如果我连续五天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我不想干了”,那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有时是失去热情,有时是对事业失恋,有时是人生有了别的召唤。一两天状态不好没关系,但要是连着几天都是,那就说明问题更深了。
Harry Stebbings:你什么时候最快乐?你觉得人生是关于快乐的吗?Nick Storonsky 上节目说过:“人生不是关于快乐,而是关于成功,只有成功才会带来快乐”。你怎么看?
Micha Kaufman:我觉得人生是关于意义。当你去追求有意义的事,过程里一定会有痛苦,也有快乐。但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只要你还在做让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内心深处就是快乐的。
Harry Stebbings: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你的孙辈以后会怎么评价你?
Micha Kaufman:我把自己看作是某种传承的一部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传给我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那些也成了我作为一个人、丈夫和父亲的核心。
我一直相信,给予比索取更有力量。我讨厌一味索取的人。也许他们会记住我是一个给予的人。这个世界不欠你任何东西,这是我教给孩子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我还跟孩子们讲,家永远是安全的地方。不管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回家,我们一起想办法。
这不是说失去判断力,而是说不要用评判去压垮他们。你的初心是帮助他们。这一点也渗透进了我的管理方式,有这种激烈但坦率的风格。
行事上,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艺术家。我通过创造来表达自己:创造一家公司、一个产品、一个社区,甚至是一场运动。
所以如果你问我想怎么被记住?一个建设者,一个艺术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格基金,作者:Neya,编辑:Cindy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End
想涨知识 关注虎嗅视频号!